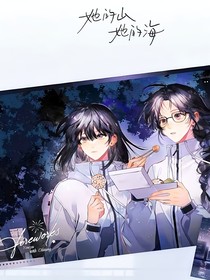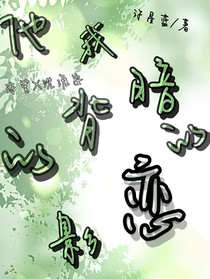重逢2
"抱歉迟到!"他咧嘴一笑,还是那个熟悉的、带着几分痞气的笑容,"刚和校队的小子们打了场球。"
文浮夏夸张地上下打量他:"哇哦,体院伙食不错嘛!"
谢星澜把篮球砸向她,文浮夏灵巧地躲开,四人笑闹着,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阳光下的天台上,四个年轻人互相打量着对方的变化,又欣慰地发现那些最本质的东西从未改变。
"带礼物了吗?"文浮夏突然问,"去年说好的,每次重聚都要带一件代表自己这一年的东西。"
四人围坐在一起,像过去那样形成一个紧密的小圈。谢星澜先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教材——《运动心理学导论》,书页间贴满了彩色标签。
"上学期最难啃的一门课,"他翻开做了密密麻麻笔记的页面,"但多亏了徐慧老师——记得训练营那个心理老师吗?她给我写了推荐信。"
简繁拿出一枚MIT的校徽和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和一群不同肤色的学生站在实验室门口,所有人都穿着白大褂,只有简繁依然固执地打着领带。
"国际学生比例37.5%,"他解释道,"社交挑战大于学术挑战。"
文浮夏的礼物是一本手写乐谱和一张CD:"我的第一张原创专辑!音乐治疗专业的作业,但老师说可以拿去正式发行。"她狡黠地眨眨眼,"里面有三首歌的歌词是墨墨的诗改编的,版权费回头分你。"
轮到肖墨墨时,她拿出了一本校刊——师范大学文学社的年度选集,目录页有她的名字和两首诗的标题。
"我...我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她轻声说,"关于一个女孩和她的四个朋友..."
谢星澜突然站起来,用力揉了揉她的头发:"我们的墨墨要当作家了!"
四人分享着这一年的故事——谢星澜和父亲的关系改善,开始定期一起看球赛;文浮夏如何在音乐与医学之间找到平衡;简繁适应异国文化的艰辛与收获;肖墨墨照顾母亲的同时坚持写作的日日夜夜。
"对了,你们去看黄老师了吗?"肖墨墨突然问。
其他三人摇头。谢星澜看了看表:"现在去?她应该在办公室。"
四人轻车熟路地穿过走廊,就像一年前他们还是高中生时那样。黄丽文老师的办公室门关着,但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她正在批改作业。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更多痕迹,依然是那个一丝不苟的发髻,那副严肃的眼镜。
谢星澜敲了敲门。黄老师抬头,看到四人站在门口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恢复了平静:"进来吧。"
办公室的布置几乎没变,就连窗台上那盆绿植都还在老位置。唯一不同的是,墙上多了一张照片——去年毕业典礼上,黄丽文和四人小组的合影。
"校庆日快乐,老师。"文浮夏笑嘻嘻地说,"我们如约回来了。"
黄丽文推了推眼镜:"大学怎么样?"
四人七嘴八舌地汇报近况,黄老师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当肖墨墨提到她的小说创意时,黄丽文的嘴角微微上扬:"苏雪知道吗?"
"知道,"肖墨墨点头,"她说...很像她年轻时想写的故事。"
黄丽文拉开抽屉——那个曾经放着"特别关注名单"的抽屉,取出四份文件:"今年的评估。"
四人惊讶地接过。文件里是对他们大学第一年表现的分析和建议,基于他们偶尔发给黄老师的邮件和朋友圈动态整理而成。
"老师..."谢星澜翻看着针对他运动心理学学习的建议列表,"您真的...一直关注着我们?"
"教师的职责不止于课堂。"黄丽文简短地说,然后指了指门外,"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还有个'星星小组'要指导。"
"星星小组?"四人异口同声地问。
黄丽文示意他们跟上。走廊尽头的小教室里,四个学生坐在特意拼在一起的课桌旁——一个戴着耳机的高个子男生,一个打扮前卫的女生,一个坐得笔直的眼镜少年,还有一个缩着肩膀的瘦小女孩。
四人组在窗外看得目瞪口呆——这简直就是他们当年的翻版。
"今年的'特别关注名单',"黄丽文轻声解释,"我借鉴了一些...成功经验。"
文浮夏的眼里闪着泪光:"您把我们当范例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潜力,"黄丽文看着教室里的新小组,"关键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和伙伴。"
她走进教室,四个新学生抬起头。黄老师开始介绍一种"互助学习模式",窗外,毕业一年的四人组相视一笑——那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传奇,现在将成为新的传统。
回到天台时,夕阳已经开始西沉。谢星澜从背包里掏出四罐可乐——就像去年毕业时那样。
"致星星小组,"他举起可乐,"无论新旧。"
"致星星小组,"四人碰杯,"永远不散。"
远处的操场上,新一届的学生正在准备校庆演出。音乐声随风飘来,混合着笑声和欢呼。四个年轻人靠在天台栏杆上,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在这个特别的校庆日,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天台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奇妙地连接在了一起。而明天,他们将再次奔向各自的远方,带着这份永不褪色的友谊,和那些被黄老师点燃的火焰。
——————
宝子们,我的第一本大纲已经更完,接下来是第二本大纲
在学校的那些件小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