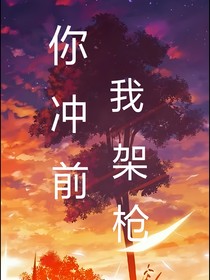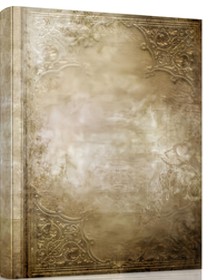第23章 你们越封我,我越想火!
林羽把警告信折成方块时,指节因为用力泛着青白。
抽屉闭合的轻响里,他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不是害怕,是某种被压抑的兴奋在窜动。
窗外的暮色漫进来,在白板上的“心灵疗愈模拟器”几个字上染了层灰,他突然转身抓起外套:“小亮,跟我去直播间。”
“现在?”正在收拾笔记本的小亮抬头,眼镜片上还沾着下午采访老张时的茶渍,“您不是说要等系统模板加载完——”
“等他们的‘正确指导’?”林羽扯松领口,手机屏幕在掌心烫得发烫,系统界面的暖金色光映得他眼尾发亮,“老张昨天说‘砍竹子时听见心里的结咔嚓断了’,这种话比任何报告都有力。我要让全行业听听玩家怎么说。”
小亮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了顿,忽然笑出声。
他抓起三脚架塞进林羽怀里,自己扛着补光灯往门外走:“您早该这么干了。上回《拆家模拟器》被物业投诉时,要不是我截了玩家说‘拆完虚拟沙发,现实里连老板的臭脸都懒得瞪’的评论——”
“打住。”林羽在电梯里调整直播设备,屏幕亮起的瞬间,他对着镜头挑了挑眉,“各位,今天不聊游戏设计,聊点真的——你们在游戏里,到底怎么撒气的?”
直播间的弹幕像炸开的烟花。
“上个月被甲方骂到凌晨,在《拆家模拟器》里把老板的虚拟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第二天居然能笑着改第18版方案!”
“玩《整蛊办公室》时把讨厌的同事P成史莱姆,现在看他真的没那么烦了……”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用游戏当情绪垃圾桶?”
林羽盯着滚动的留言,喉结动了动。
他想起昨天在老张家,那个总把“忍忍就好”挂在嘴边的老木匠,举着虚拟斧头砍竹子时,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此刻弹幕里的“终于有人愿意听”像滚烫的石子,一颗一颗砸在他心上。
但热度涨得有多猛,批评来得就有多快。
深夜两点,小亮揉着发红的眼眶把手机递过来:“《都市晨报》说您是‘情绪焦虑贩子’,《游戏观察》质问‘诱导砸东西和鼓励极端行为有什么区别’。”
咖啡杯在林羽手下转了个圈,褐色液体晃出涟漪。
他点开那篇报道,“贩卖”“诱导”这些词像尖刺扎得他太阳穴发疼。
但当他翻到评论区,看到玩家们自发贴出的情绪日记——“玩完游戏后去做了心理咨询”“和妈妈大吵一架后,在游戏里学会了说‘我很难过’”——他突然笑了。
“把老张的脑电波数据调出来,还有李女士的情绪曲线对比图。”林羽拽过椅子坐下,屏幕蓝光在他脸上割出锐利的棱角,“我们要写一份白皮书,不是给那些评论家看的,是给所有在游戏里找出口的人。”
接下来的48小时,办公室的灯光就没熄过。
小亮抱着一摞学术论文冲进来时,林羽正对着屏幕敲代码:“社会心理研究所的王教授说,我们的玩家情绪转化率比传统疗愈手段高37%?”
“还有这个!”小亮把平板拍在桌上,是某高校心理学系的邮件,“他们要把我们的案例放进教材。”
林羽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住。
晨光透过百叶窗洒在他发梢,他突然想起穿越前那个在格子间里敲代码的自己,每天下班时天都黑透了,连句“我好累”都不敢说。
现在屏幕上跳动的,是玩家们用游戏记录的“我生气了”“我害怕了”“我好多了”——这些真实的情绪,不该被封在“负面”的标签里。
《情绪释放型游戏白皮书》发布当天,林羽的手机炸成了蜂窝。
“林先生,我是XX游戏公司的主策,我们想合作开发疗愈模块!”
“林老师,能把您的情绪转化模型共享吗?我们社区想用在青少年心理辅导上。”
小亮举着手机冲过来时,林羽正盯着新游戏的开发界面。
虚拟城市的轮廓已经成型,穿西装的白领在虚拟办公室里深呼吸,被家暴的主妇在游戏心理咨询室里攥紧纸巾——这些曾经只能在现实里沉默的人,终于有了发声的地方。
“测试版上线半小时,下载量破十万!”小亮的声音带着颤音,“玩家说‘这哪是游戏,这是我的另一个人生’!”
林羽点开测试反馈,第一条留言就让他红了眼眶:“我在游戏里和爸爸和解了。现实里,我打算明天回家吃饭。”
他正想把这条留言转发给小亮,门铃突然响了。
送快递的小哥举着EMS信封:“林先生,您的急件。”
封口处的“文化监管部门”红章在阳光下格外刺眼。
林羽捏着信封的手微微发颤,拆开的瞬间,“三日内提交审查材料”几个字像一盆冷水,顺着后颈往下淌。
办公室里,新游戏的测试界面还在闪烁,某个玩家的情绪进度条正从“压抑”缓缓爬向“平静”。
林羽望着窗外渐起的晚风,突然笑了——上回被协会警告时,他说要证明游戏是镜子;这回,他要让这面镜子,照得更亮些。
他转头看向还在盯着手机傻笑的小亮:“把测试数据整理成可视化报告,再联系王教授要份学术背书。”
小亮愣住:“您不打算——”
“硬碰硬?”林羽抽出一支红笔,在“审查材料”几个字下画了道粗线,“我要让他们看看,玩家的情绪,值得被认真对待。”
窗外的蝉鸣突然响了起来。
林羽翻开空白的审查材料,笔尖落下的瞬间,阳光正好漫过他笔记本上的一行字:游戏从不是问题,如何面对情绪,才是。
游戏天才基本法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末日进化乐园
- 上一世,末世来临,他真诚善良,守护所有人,最终,却被人诬蔑为反人类的邪恶魔头,成为天下公敌,被人类所不容,谁也不知道,曾经走在抵挡末世异族最......
- 341.1万字8个月前
- 游戏王BWF
- 算是我第3本游戏王小说了,老规矩,还是大师规则。这本的世界观是续着《游戏王LAR》的。和《游戏王JDW》换着更新。
- 23.3万字7个月前
- 做局(对家就想玩死你)
- 本就阴差阳错,谁料天宫不做美偏做局,一个网络白痴,一个游戏高手,输赢胜负,各安其命!
- 2.9万字6个月前
- 穿越到地域之诗当中?
- 有双厨哦
- 0.8万字6个月前
- 你冲前,我架枪
- 17岁的许一夏因为学校的劝退走上了电竞之路,他入职sky俱乐部,对于一个合格职业选手来说,他只是一位狙击精准度高的决战玩家,开局因为一句粉丝......
- 1.6万字5个月前
- 游戏图鉴
- 1.5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