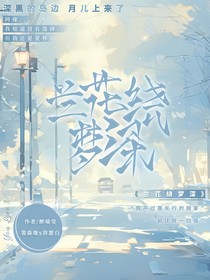并肩的力量
连续一周,苏漾的办公室都亮着长明灯。电脑屏幕上的数据模型像一团乱麻,无论她调整多少参数,模拟结果始终卡在同一个阈值,像被无形的墙挡住了去路。桌上的咖啡杯空了又满,折到一半的纸鹤被揉成一团,边角泛着疲惫的褶皱——那是她思考时的习惯,指尖无意识的动作总能帮她梳理思绪,可这次,连纸张的纹路都透着固执的滞涩。
“又卡住了?”林砚舟推门进来时,撞见她正对着屏幕皱眉,指节抵着太阳穴轻轻按压。他把温热的牛奶放在桌边,视线扫过屏幕上跳动的红色警告线,“港珠澳大桥的抗风抗震参数要求本就严苛,你想在传统模型里融入折纸的立体支撑结构,等于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苏漾没抬头,声音带着熬夜后的沙哑:“可这明明是最优解。折纸的蜂窝结构能分散应力,就像纸鹤翅膀的弧度能抵消气流阻力,原理是相通的……”话没说完就卡住了,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可为什么模拟结果总是不稳定?是不是我太异想天开了?”
林砚舟没说话,只是弯腰捡起地上那团被揉皱的纸鹤,小心翼翼地展开。纸张边缘已经起了毛,但能看出原本的折痕试图勾勒出一对不对称的翅膀——那是苏漾独有的折法,左边翅膀比右边宽出半厘米,却总能让纸鹤飞得更稳。“你以前教我折的时候说过,不对称未必是缺陷。”他把纸鹤放在键盘旁,“要不要换个角度?比如先不管数据,单纯想想折纸时,你是怎么让这只‘歪翅膀’保持平衡的。”
苏漾盯着那只伤痕累累的纸鹤,突然觉得眼睛发酸。这阵子她像钻进了牛角尖,反复核对力学公式、调用数据库里的桥梁案例,却唯独忘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那些被她视为“不务正业”的折纸时光里,藏着最朴素的结构智慧。她猛地合上电脑:“我想出去走走。”
车子驶出市区时,夜幕正悄悄拉开。林砚舟把车停在海边,咸湿的风卷着海浪声扑面而来。十月的海边已有凉意,苏漾裹紧外套走到礁石旁,看着海浪一次次撞向黑色的岩壁,碎成雪白的泡沫,又退回去,积蓄力量再次冲锋。浪花溅在礁石上,打湿了她的鞋尖,带着大海特有的腥甜气息。
“你看它们多固执。”林砚舟站在她身侧,声音被风声揉得很轻,“科学家说海浪的运动有规律,可在我看来,它们更像一群不肯认输的孩子。撞疼了就退远些,攒够力气再冲上来,从没想过要绕开礁石。”
苏漾的目光追着一波海浪,看它在礁石上撞得粉碎,却又借着回流的力道,在不远处托起一朵小小的浪花。“可它们好像……也没真的过去。”
“但它们改变了礁石的形状啊。”林砚舟指着礁石底部被冲刷出的凹槽,“千百年下来,再坚硬的石头也会被水滴石穿。你现在遇到的,或许不是需要‘跨过’的墙,而是需要‘打磨’的礁石。”他捡起一块贝壳,在掌心转了转,“你的折纸结构是优势,别因为暂时的不匹配就否定它。就像这贝壳,原本是柔软的蚌壳,被海浪磨出棱角,反而成了独特的存在。”
海风掀起苏漾的长发,她突然想起小时候在澜沧江边折纸船。有的船被漩涡卷走,有的撞上石头散了架,但总有一两只,借着水流的弧度绕过障碍,晃晃悠悠驶向远方。那时爷爷总说:“水是活的,船也得是活的。”原来她一直想让折纸结构“适应”模型,却忘了该让模型“包容”折纸的特性。
回到工作室时,天边已经泛白。苏漾重新打开文档,删掉那些刻意贴合传统模型的参数,转而把折纸时“预留缓冲空间”“不对称平衡”的思路写进去。指尖敲击键盘的声音变得轻快,像纸鹤展开翅膀时的振翅声。当她将最后一组数据输入模拟系统,屏幕上的红色警告线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流畅的绿色曲线,像海浪般起伏,最终稳稳落在安全阈值内。
“我成功了!”她抓起手机拨通林砚舟的电话,声音里的喜悦像要溢出来,“模型通过了!你说的对,它不需要变成别人的样子,它自己就可以站稳!”
电话那头传来低低的笑声,带着显而易见的骄傲:“我就知道你可以。”背景音里隐约有抽油烟机的声响,“晚上别吃外卖了,我买了新鲜的鲈鱼,做你爱吃的糖醋鱼庆祝。”
挂了电话,苏漾看向窗外。晨光穿过云层洒在楼顶上,给冰冷的钢筋混凝土镀上一层暖金色。她想起林砚舟在海边说的话,突然明白,所谓并肩前行,不是两个人走在同一条直线上,而是像海浪与礁石,一个给予力量,一个学会包容,在彼此的支撑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桌上那只被揉皱又展平的纸鹤,此刻正迎着晨光,歪着翅膀,却仿佛随时能飞向天空。
漾光折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