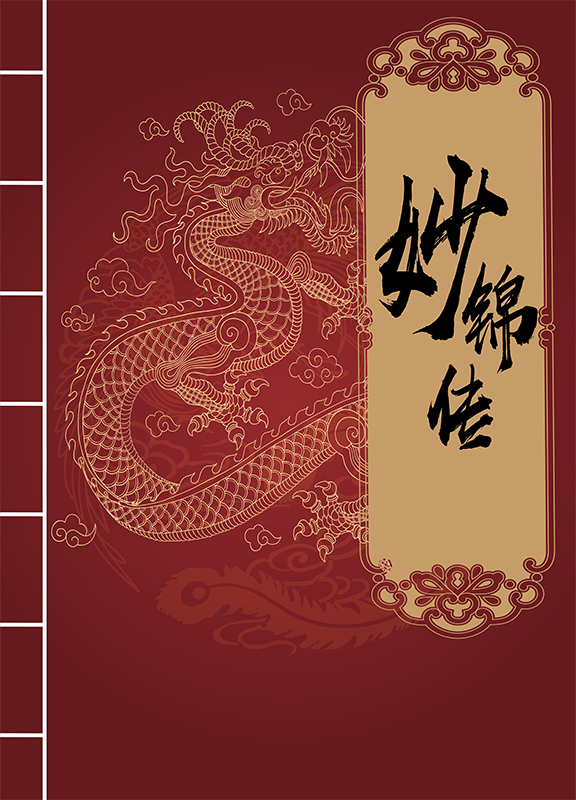第七十八章款战之争
所谓通款,一般指的是交涉,求和。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列阵于长江北岸之时,建文帝曾用方孝儒通款之议,许以割地划江而治,遭到朱棣的拒绝。当日建文帝以太祖嫡孙、君临天下四年之久的皇帝之尊屈膝求和尚且不可,如今北京的那位戾君已明发诏书,将南都诸人打为逆案要犯,且王师已突破长江天堑,克复南都已是指日可待,朝廷还有什么本钱与北京的那位戾君议和?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投降而已!
无疑,这也是每个人心中早已设想过的一种选择。但是,每个人心中也都是顾虑重重:且不说北兵尚未兵临城下,此刻就贸然提出投降似乎为时未免过早,会遭到朝野上下清议的抨击;也不说放弃维护道统祖制的理想,向北边的那位戾君再度屈膝称臣,是多么可耻可羞的一件事,更逃不过苛刻的公论和无情的史笔的责难和鞭挞;单说投降之后能不能保全自己乃至全家老小的性命,也还是个未知数——谋逆是灭门的罪,而一部《二十一史》从来只有诛灭九族,惟独大明朝,却可以诛灭十族,首遭此前所未有的惨祸的,不就是在皇权斗争中站错了队的方孝儒吗?情势如此危殆,倘若一步踏空,便会万劫不复。说起来,毁不该当初真只想着靖难功成便能杀回北京重掌权枢,将身家性命全压在这场豪赌之上,一点贪念,到头来连老本都输得精光!
此外,即便他们这些臣子能幸蒙圣恩,罢官致仕、贬谪充军,乃至抄没家产、身送东市,大概也总能留下一点香火后嗣,不至于成为“若熬之殍鬼”,更不用担心祖宗祠墓无人祭扫,成为家族宗庙的千古罪人。而那些勋臣贵戚们,如魏国公徐弘君、信国公汤正中和诚意伯刘计成等人,南都起事之后,他们干了多少非人臣所敢为之事?天恩再浩荡,也浩荡不到他们的头上,终究还是难逃抄家灭族之祸。这种情况下,他们怎能同意通款之议?姓蔡的一心只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提出通款之议,只怕已将那些勋臣贵戚得罪到了死处,人家手中有刀帐下有兵,焉知就不会狗急跳墙,在北兵到来之前就先把他给抄家灭族了?自己若是赞同此议,岂不要受他池鱼之灾?
想到这里,有人立刻就坐不住了,想要严词诘难蔡益身为朝廷肱股重臣,竟如此怯懦,意欲献城投降,苟且偷生。但是,就在那些话即将脱口而出的一瞬间,又咽了回去。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在蔡益提出这个名为通款,实则投降的主张之后,大堂上又变得一片沉寂,固然没有人发言表示赞同或是反对,连勃然变色或是颌首默许的都没有,仿佛是坐了一群泥塑木偶一般。
更令他们感到意外和疑惑不解的是,坐在上首的三位勋臣,无论是徐弘君,还是刘计成,仍旧是一动不动地坐着,象是根本就没有听到蔡益方才说了些什么;只有汤正中缓缓地捋着胡子,象是在沉思,脸上却根本看不出有什么赞同或否定的表示。
这样的反应提醒了那几位冲动的大臣:姓蔡的靠着小老婆的裙带关系当上大宗伯,平日里与那些勋臣贵戚打得火热,他那个曾是秦淮名妓的如夫人更是凭借当年在旧院开门迎客之时,与魏国公徐弘君等勋臣贵戚结下的“交情”,日夜穿梭于权贵之门,还因她已将徐弘君的宠妾认为干娘,便时常留宿于中山王府,会否是在“承欢膝下”、侍奉枕席之时,听“干爹”流露出一星半点通款的意思?因投降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依徐弘君的脾性,自然不方便也不好意思自己说出来,“干女婿”蔡益这才为“父”分忧,当众提出了通款之议。若果真如此,到头来人人都附议行款,那么自己若是贸然反对此议,岂不得罪了那些凶神恶煞的勋臣贵戚?这且不说,倘若张扬了出去,传到北边朝廷那里,岂不更是大大的不利?
想到这里,他们都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暗骂自己糊涂,并赶紧屏息低头,摆出了和大多数人一致的漠然神情,似乎这件事情全然与自己毫无关系一般。
不过,无论行与不行,蔡益的通款之议毕竟为众人指示了一条可以选择的出路,而且,情势确已危殆至此,枯坐于此也不是办法,大堂上渐渐有了生气,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嘤嘤嗡嗡的声音响成了一片。终于,有人起身,冲着坐在上首正中的徐弘君一拱手:“敢问徐公,目下京营之兵,尚有多少?”
发问之人是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伟业。此人原本只是兵科都给事中,靠攀附勋臣权贵,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益辽之争后,朝廷多位大臣拜疏求去,他又升任左副都御史,因其师、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张履丁也挂冠而去,都察院便由他实掌院事。不过四十出头的年齿、短短数月之内,就由六品给谏擢升为正三品左副都御史,更在事实上成为位高权重的“总宪大人”,乃是国朝前所未有之殊荣,朝野上下、道途之中,无不为之侧目。
被指名问到头上,徐弘君也不得不抬起了头,漠然地看了吴伟业一眼,艰难地将肥胖的身子在座椅之上挪动了一下,这才回答道:“不论城外守军,只城中如今就有二十万之众。”
“二十万京营将士想必俱是国公老大人一手**之劲旅精兵。我朝兵势如此之盛,全赖国公老大人公忠体国、治军有方啊!”吴伟业热烈地说:“北兵远来疲敝,我兵以逸待劳,背城借一,尚堪一战。去岁北京为北虏所围,便是如此破而胜之。况且留都城池坚固,兵甲火器粮储甚多,绝不在北京之下。我等只须坚定心志,固守城防,并传檄浙江、湖广等省,召各省守备之兵及镇南侯安思达、靖远侯杨士冲之南蛮异族之兵回援南都。假以时日,待四方勤王之师齐聚城下,纵使不能一鼓破敌,也能将北兵驱而退之,又何必怯懦至斯,仓促言款,全然致君子之操守、人臣之名节于不顾?”
方才蔡益提出通款之议,已然被众人在心里嗤之以鼻,而此刻吴伟业如此慷慨激昂地反对投降,不但被众人认为是痴人说梦,甚或更认为是荒谬绝伦。尤其是听他比出去年北京保卫战之事,并称要仿效前例,召各省之兵勤王,众人同时心中一凛:这个欺师背主的奸佞小人,若不是被气势汹汹的北兵吓得昏了头,便是早有异心,意欲效法赵高乱秦之事,祸国乱军,将大家全置于死地啊!
最为气愤的,自然是提出通款之议的蔡益,尤其是当他听到吴伟业当众说自己“怯懦”、“致君子之操守、人臣之名节于不顾”之类的话,更是怒不可遏,当即愤然起身,用那双几乎要喷出火星的眼睛狠狠地瞪着吴伟业,说:“京营皆是劲旅精兵,自是不假。但国公老大人一手**之靖难军及诚意刘伯之江防军,又何尝是疲兵弱旅?况且其数倍于京营之兵,尚不能保有徐州坚城、长江天堑。如今欲以区区二十万人,御北兵乘胜之师,岂非妄想!”
说着,蔡益突然提高了声调:“亏你吴副宪昔日曾为兵科给谏,竟敢做如斯之想!迂腐书生,只以坐论空谈为能事,误国误军,罪莫大焉!”
其实,吴伟业只不过是以为那些已犯下不赦之罪的勋臣贵戚们是断然不会答应通款之议的,为了答谢勋臣贵戚们的赏识拔擢之恩,才率先表明立场,反对此议。加之这半年来,他春风得意,好事接连不断,尤其是实掌都察院,手握纠察弹劾大权之后,更是风光一时无两,根本就没有把平日里糯米团子一样的礼部尚书蔡益放在眼里,因此说话也就不留情面。听到蔡益抗辩,他那张扁平的脸上便浮现出了刻薄的冷笑:“留都乃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地,江南民心,维系于此。我辈臣子,世受大明厚恩,若不战而降,试问将有何颜面以对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
吴伟业与蔡益一样,都是那帮勋臣贵戚的门下走狗,他如此激烈地反对投降,令在场的人都不由得猜测,莫非这才是徐弘君、刘计成等人的本意。可是,当他们偷偷打量那几位勋臣贵戚的脸色之时,却发现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实在让人猜不透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依年齿,论资历,吴伟业都没有这样当众与蔡益争吵的道理,他的嚣张气令许多年高望重的大臣们十分不满,南京吏部尚书杨士聪、户部尚书刘泌等人纷纷参与进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貌似劝说,实则指责起了吴伟业:
“吴副宪不必如此。蔡大宗伯不过是出此一议,至于款与不款,尚可从长计议。”
“留都不只是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地,更是太祖高皇帝与孝慈贞化哲惠仁徽成天毓圣至德高皇后陵寝所在,一旦开战,势必震惊梓宫。我辈臣子,又焉能不虑之忧之!”
“留都百万生灵皆系于我辈一念之间。惟有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方可免于涂炭!”
遭到了围攻,吴伟业的那张脸越涨越红,马上就要发作起来,与他颇有私交的南都詹事府詹事陈于鼎担心他不是那帮倚老卖老的大臣们的对手,强逞口舌之能只不过是徒取其辱而已,便出面排解了:“哎,时危势迫,相争无益。我等还是且听魏国徐公、信国汤公并诚意刘伯如何处置吧!”
陈于鼎此言可谓一语中的——是啊,如今留都当家人是那些勋臣贵戚,是战是降还轮不到他们来裁夺,争来争去有什么劲儿呢!因此,所有人都闭了嘴,将目光投向了坐在上首的三位勋臣。
我欲扬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之大明国公
- 简介:一次意外,让张凡这个经济专业的高才生穿越到大明朝。不一样的身份,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生。他到底会如何度过!已经设定好的人生道路带他走进了大明政权的权力中心,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又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且看张凡这样一个穿越人士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大明朝的巅峰!【纯属虚构,请勿模仿】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677.6万字6年前
- 抗日之精英特战队
- 简介:【《抗日之精英特战队》将于2013.03.13开始限时全本免费读为期3天】穿越到了1931,又恰逢日寇侵华,身为男儿自当舍身抗日;号称恶魔教官的罗霄,率领麾下虎牙特战队穿越到了民国,于是投身抗日洪流之中,开始了抗击日寇的征途……龙战于野、泣血山河,一路杀得日寇抱头鼠窜,闻其名丧胆……带去的装备用完了?没关系,咱有超级兵工厂,更暴力更强大的武器将继续蹂躏日寇!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本故事纯属虚构,只供娱乐,请勿模仿;发生地点为平行空间,如与历史偶似,乃是巧合!!!★★★红色尖兵战队总部群:32451897YY频道:25905993***************推几本朋友力作:神界圣主,囚情:误撩君心,七魄鼎天,仙宫……,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哈!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51.9万字6年前
- 大明1937
- 简介:“大明五日游。”现在一日,明朝一年。主角到了明朝后,才发现:时间不对——1935?!而且,北方还是清朝的天下…… 北清是君主集权,南明是君主立宪。北清首都离边界有1000公里,南明首都离边界只有1000米。但是,南明有主角。 20世纪明朝人穿什么?挣多少钱?20世纪的东厂和锦衣卫是什么样子的?20世纪的大明皇室和内阁,谁听谁的?明、清之间的坦克战怎么打?大明潜艇如何封锁日本列岛? 书友群:78257491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382.7万字6年前
- 东渡战国记
- 他,来到了日本战国时代;他,想要改变未来的历史;他,必须杀死织田信长;他,活了下来!
- 9.7万字4年前
- 妙锦传
- 中国明朝,这个国祚近二百七十余年的大一统王朝,在历史上因其辉煌与黑暗并存的特殊性,一直以来为众人所津津乐道。至千禧之年而下的二十余年里,这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朝代总是被掩盖着一层朦胧,有人唾弃其厂卫的阴狠恶毒,亦有人颂扬其威震八方的天朝国威。但无论怎么说,象征这个朝代的符号总是让人屡屡惊叹。《永乐大典》,《本草纲目》,《纪效新书》亦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难以磨灭的光辉星辰。扫荡安南,南驱倭寇,北攘蒙古,壬辰战争,铿锵铁马之声至今仍旧回旋于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七下西洋,宣仁之治,火枪,紫禁城,内阁等等诸如此类,频频成为历史大家们热烈讨论之对象。三次盛世,两次中兴,一次革新。在古典王朝中,这是极其少见的。而明朝自开国以后,平均五十年就出现一次极度繁荣的社会现象,亦不可不为之惊奇。诚然,脱离洪武之治来浅谈永乐盛世无异于空中楼阁。那么,这个开国仅仅以半个甲子的时间,就快速步入巅峰的王朝,它的背后,究竟又隐藏了什么?又是谁铸就了宏伟的永乐盛世?在这盛世中,又隐藏了多少悲欢离合?请让我们慢慢走进明朝,去细细感受它给我们带来的别样美感。
- 12.1万字4年前
- 我要做列强
- 刘般和网管小妹在网吧触电穿越时空来到了一个与地球相似的世界,这里也有列强在用坚船利炮征服着一个有一个落后的国家,也在掠夺着无数本该不属于他们的资源财富。看刘般如何与网管小妹如何利用系统帮助,使一个东方大帝国变成列强们的噩梦。其实就是猪脚利用系统大大的帮助与网管小妹笑傲新世界的过程。
- 4.5万字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