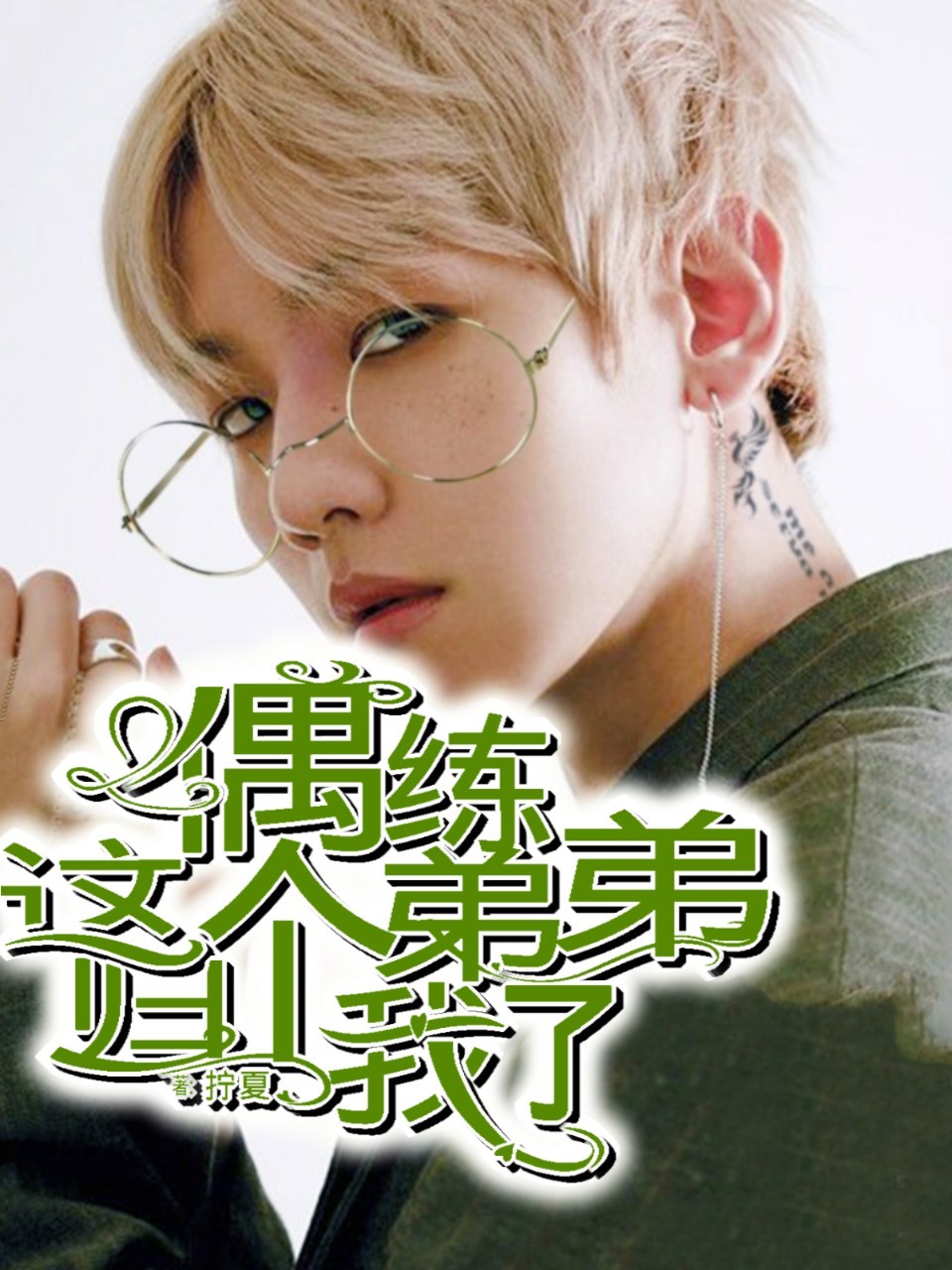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水汽缭然,夜深风静,火光熠熠,金鳞点点。
我似乎抱着谁,
白夭夭:他是白帝么?
可我似乎并不喊他‘白帝’,而是另一个称呼,
白夭夭:‘辰郎’?辰郎是谁。
我好像对那人说了一句话,然后便听见他低低的一声笑,似乎就要朝我伸手过来。
他将我压在身下,温热的湖水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床榻,他吻我,我轻喘,星光落进我的眼里。风变热了。
一夜巫山,一晌贪欢。
我猛然睁开双眼,从梦里醒了过来,掀开身上的薄被,一时只觉得身上热极,我背心不知不觉已被汗个湿透,衣衫黏在身上,感觉甚不舒坦。
白夭夭:方才所做的梦,想来太半就是传说中的春梦了?
我兴致甚好地想了一想,
白夭夭:从前只在话本戏曲里面见过小姐春梦会情郎的情节,以为人类想象力甚是丰富,竟能把个虚头巴脑的物事描述得好似真的一般,没成想原来春梦一说确有其事。
白夭夭:我今日倒也做了一回杜丽娘,可惜到底是错过了春天,夏天做春梦,终究有些不太应景。
借着半开的窗,我吹了吹风,凉快了一会儿。
顺道看了一眼窗外之景,就见不远处的树下不知何时栓了一只高壮的山羊,白帝正堆了一堆鲜嫩的树枝给它喂食。
白夭夭:“喂,”
我趴在窗台边问他,
白夭夭:“这山羊从哪来的呀,难道是你猎来的?”
白夭夭:白帝打野味的本事倒是见长么,居然都能猎到山羊了?
白帝抬头看我一眼,摇了摇头,道:
白帝:“它自己跑来的,我也不知道这羊是从哪里来的。”
我拍了拍手,指了指那山羊,笑道:
白夭夭:“我看这山羊长得甚是结实,四条腿的肌肉很是发达,看上去是个当坐骑的好羊,不知辰郎你意下如何啊?”
白帝蓦的脸色一变,道:
白帝:“辰郎是谁?”
我一噎,霎时想到了自己方才的那桩春梦,瞬间热透了脸,我下意识地捂了捂脸,继而又想起现下正是炎炎夏日,我们蛇本就容易在这样的温度下沸血脸红,便放下手,若无其事道:
白夭夭:“口误,口误而已,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之前的那句话,这羊看上去很适合当咱俩的坐骑,骑上它赶路,也省得我俩脚疼腿痛了,你不觉得?”
白帝沉默一阵,点了点头,向我道:
白帝:“不知道你打算何时动身?”
摆了摆手,我道:
白夭夭:“这不是看你的决定么,我反正就跟着你走,你打算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只要不是现在就行。”
白帝:“那就后天吧,今明两天可以备些干粮。”
白帝回话道,他语气有些欣喜,又有些郁郁,当真好生奇怪。
白夭夭:这恐怕是吃那个‘辰郎’二字的醋了,可惜他不知道我梦里的‘辰郎’就是他嘛--不过这件事我可不会这么轻易地就告诉他,反而还要好生让他吃几天醋,伤几回心。
白夭夭:哼,谁让他不由分说就关我两个月的小黑屋来的?还有青儿--她和法海可真是无妄之灾,哼,我可是条小心眼的蛇。
这般心里想着事儿,我起了床,抬手随随便便挽了个发髻,正要出门去舀水洗脸,忽然发觉自己方才的视线角落里似乎多了点什么东西,于是扭头一看,就见那床头小几上摆着两只碗,一碗里是蘑菇汤,一碗里是杂菜鸡蛋羹。
转了转眼珠,我扑哧一笑,当下又从窗子探出头去,道:
白夭夭:“原来你已经会做饭了啊,那看来没有我什么事儿了,那我俩如今就可以江湖不见了,对吧?”
白帝道:
白帝:“什,什么?”
只见他原地站了一会儿,忽然飞身跑过来,和我隔着窗框,向我道:
白帝:“那可不行,你,你会做肉食,我只会这一汤一羹,不行不行,你走了只怕我是要饿死。”
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勉力止住想笑的冲动,道:
白夭夭:“一法通则万法通,你自己琢磨几回,总会变得厨艺高超的。”
白帝道:
白帝:“那也不行,我如今法力未复,你走了之后,遇见危险我又该如何面对?”
我将自己的语调扯地甚是无情:
白夭夭:“短短数天,你的法力已经从无到有了,如今却还愁什么法力未复?重回巅峰对你来说其实是迟早的事儿,迟早的事儿。”
白帝的神色立时厌厌下去,半晌,但见他低头勉强一笑,向我拱了拱手,道:
白帝:“如此说来,如此说来,多谢这几日白姑娘你的照料了,在下感激不尽,如有来日,必当结草衔环。”
我暗笑一声,表面上却作出一副慷慨的表情,亦朝他拱了拱手,道:
白夭夭:“大家都是同道,谈什么结草衔环,真是好生迂腐,我给你做饭几日一事,原来也不过是桩交易,你已为我暖了被窝,如今也可算是钱货两讫了。”
听完我的话,白帝表情更恹,嘴里的话却更见恭敬疏离,道是:
白帝:“白姑娘说的是,是我迂腐了,不知白姑娘打算何时离去?”
指了指那早餐,我道:
白夭夭:“嗯,我吃完早饭就走,顺道也可品评一下你的做饭手艺。”
白帝向我作了一揖,礼数极为周到,向我道:
白帝:“品评我的手艺,那便多谢白姑娘了。”
我笑呵呵回他一揖,道:
白夭夭:“好说,好说。”
等我吃完早餐,抹了抹嘴,便向白帝告辞,白帝面色冷冷清清,倒有了几分灰败的意态。
而后我便化为白蛇原型在山间穿梭来去戏耍鸟兽,自觉倒比用人身时畅快许多,中途我又悄悄回了小屋看了白帝几次。等到日色西沉,白帝他开始收拾行囊,顺道又喂了山羊一回。
小憩一时,我打着瞌睡再去看时,小屋里已然是人走茶凉。
顺着山羊行路的蹄痕,我发现那山羊被拴在了一棵小树边,不远处是一条净澈澄明的小溪,水声哗哗,溪边石块上搭着几件衣衫。
白帝:“谁?”
白帝蓦的睁开双眼,我化作人身,捧了一捧水,往他头上泼去。
白帝:“白夭夭?”
溪水浇头,白帝的脸腾腾红起来。
我打量着他,只觉得他透红的脸尤其别致,道:
白夭夭:“云雨巫山,请君共赴,君愿否?”
白帝瞠目结舌,半晌,结结巴巴道:
白帝:“固,固所愿也,不,不敢请耳。”
白帝和我嘴唇相触,皮肤相贴,他生涩地吻我,热情极了。我们的发丝湿漉漉缠在一起,我抱着他的头妄图他更贴近我,他揽着我的腰希冀我更贴近他。
一吻毕,我们的嘴唇微微分开,正要回味亲吻的余韵,山羊扫兴地叫了两声,约莫是吃树叶吃得欢了,我的头皮也扫兴地疼了一疼,原来是我和白帝的头发缠作了一个死结。
我哀声一个长叹,开始认命地解头发的结,白帝的嗓子里透出一个闷闷的笑来。
白帝:“我爱你。”
白帝道。
我嗯了一声,信口道:
白夭夭:“我知道啊,你前天不是就说了,你对我动了情么。”
白帝沉默良久,伴随着深沉打量着我的双眸,他道:
白帝:“你不喜欢我,我虽是伤心,可一想到,一想到等到了我断情那一天,你也不会因此而受伤,我就也有些释怀了,但,但,求你别同旁人再做这样的事,起码在我对你断情之前,行不行?就当怜悯一下我这个老光棍,好么。”
我疑惑,道:
白夭夭:“什么这样的事?”
他眸光甚是专注,棕黑的眼睛在不甚明亮的水光里显得极幽极深,我被他这样凄苦的凝视看了一瞬,忽然就明白过来他是在说什么,当下向他展颜一笑:
白夭夭:“你这是独占欲,要不得呀,要知道,我这样的美人自然是属于很多人的。”
白帝面色一沉,看他吃瘪似乎别有兴味,我乐得哈哈一笑,这才又道:
白夭夭:“不过么,我这小妖向来善解人意,既然你诚意相求,那我--”
拉长了声音,看着白帝那张脸上渐渐浮起的希冀,我偏偏头,
白夭夭:“我要考察一番,看看你值不值得,你还不快来同我共登极乐?”
白帝脸色一白,又再度涨红,他低头要来再次吻我,我忽然想起一事,忙道:
白夭夭:“水里不成,一会儿头发又要打结,我们去岸上,去岸上。”
白帝:“都听你的。”
白帝殷殷向我低语。
人类的身体温热,掌间沟壑毫无章法摩挲着我的皮肤,我双手撑在他腰边,蛮用力地拧着地上的草叶,在他身上肆意,如鱼得水,似旱逢霖。
我的身体还在,意识却像是飘远了,似乎有一种香气萦绕在我的鼻尖,像是薄荷,又像沉檀,比龙涎香更加清冽的香气弥漫,我张了张嘴,想唤些什么,嘴边几乎就要溢出辰郎二字。
白夭夭:辰郎到底是--
忽然,白帝翻身一把将我压下,自喘息间泄出一句支离破碎的话来:
白帝:“少昊,叫我,少昊。”
白夭夭:“少,少昊。”
我回过神,香气消失。
月色隐没,日色渐渐自东方亮透,树荫间透出点点光斑,好似我那一场梦里的漫天星光。
水声潺潺,山羊低叫。
白夭夭:这左右不过是一场春梦引发的糊涂账,我白夭夭什么都没有承诺他,自然可以穿上衣服就此甩袖走人,然而,然而。
我躺在白帝身侧,竟觉得就这样对他许下一生之约,似乎未必不行,幸好顷刻间就想起了锁妖塔和青儿,立时,我热乎乎脑子就清醒下来。
起身穿衣之际,我随口问他:
白夭夭:“你放才为什么要我叫你少昊?这称呼可有什么来头么?”
白帝松松罩好衣袍,沉默着替我系衣带。
我又问。
白帝道:
白帝:“我生在一个穷奢极欲的皇室,我出生前天下大乱,流民四起,父皇笃信祭司之言,觉得那些流民的出现并非是因为他为政暴虐,是以带着我母后前去王陵灭魔。”
白帝:“说来也奇,我母后去过王陵的当夜,就梦见五色神气入怀,然后便有了我,我父皇得知此事后,命祭司查经阅典,得出此乃当初神州始祖少昊出生时的异像,是以不顾大臣和我母后的反对,强行为我取名为少昊。”
白帝:“后来我拜师昆仑,师父又为我重新取名招拒,就在我成为白招拒的两年之后,父皇被人砍下头颅颠覆了皇朝。”
他揽过我的手,紧紧握住,又道:
白帝:“我虽然知道父皇他是死有余辜,但是他死之前对我的关爱却从来都作不得假,我很怀念有人叫我少昊这个名字的感觉,一千多年了,我一直压抑着这种怀念,唯恐被人知道自己其实是个从不真的关心所谓苍生的伪君子。”
心怀苍生的白帝说出这样一番话来,这却叫我不甚惊讶,人类总是如此,我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失望,似乎在想,原来白帝也不过如此。
白夭夭:我修仙问道,行走神州,数百年见闻之间,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纯善的小白蛇了,千百年间,我从未见过一个完人,也见过不知多少个伪装出的圣人。
白夭夭:完人不可得,圣人不可追,神州之内,似乎也仅仅只有五帝尚可以接近我所憧憬的那种‘真神仙’,其中当属白帝的名声最应清虚。
白夭夭:他还差最后一步便可以断情证道,我便以自己为代价,给他这个证道的机会,让他走完这条绝情弃爱的路。
白夭夭:我想见到真神仙。
白夭夭:可惜他终究只是一介凡人。
白夭夭:“少昊,”
我唤了他一声,然后道,
白夭夭:“我其实也一直觉得苍生这个概念还挺泛泛的,似乎谁都能关心一下,又谁都能抛弃一下,其实照我来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觉悟也就够了,再大的觉悟,听起来是很大爱,其实就是对身边人无情的借口。”
白帝侧头看了看我,亲了亲我的额头。
香蜜之三生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狗七封面铺(本人联考关铺两天)
- 简介:❗格式和收费请看第一章,必须看❗本人脾气时好时坏,别来催单,可以给你笑脸,也可以直接把你删了❗【简慕文社❤️简烟书璐竹,慕义久成都】这里是七欲,随时在线陪玩,抱图dd并且关注我,盗图我会直接来找你【注意:不接甜封,男频,古风】擅长伪橙光,溶图,同人,欢迎来评论区下单哦铺子不招美工◇钟意许又言◇女神沈川vivi◇初心阿难◇超爱西歪◇男神愉愉◇【QQ:3307019112】【部分素材源于网络,侵权致歉】
- 0.9万字6年前
- 陈情令:忘羡情归
- 简介:“本是少年郎,无羡更无忧”一朝重生,与忘机情归
- 0.8万字5年前
- 斗龙战士之复仇之旅
- 简介:关于小熠复仇
- 0.1万字5年前
- 吾王变成小孩纸了肿么办?
- 简介:天哪!堂堂怪物首领,说变就变成了萌娃!王者风全都木有了。。QAQ这样紫该肿么打架了吖…
- 2.3万字5年前
- 陈情令之心之所动
- 简介:不一样的陈情,一样的忘羡;不一样的剧情,一样的甜。
- 22.9万字5年前
- 偶练:这个弟弟归我了
- 简介:[八句馆]唯愿风雨吉祥,处处皆是八句馆禁抄袭,禁借梗,禁转载,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在这里,你将看到咱们的主角从未来重生而来,获得了可爱的系统,然后参加了偶练这个节目,将会与他们发生怎样的事情最后到底谁为谁失了心❤️让我们敬请期待文中金手指,主角光环比较强,有点玛丽苏,不喜者慎入
- 5.5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