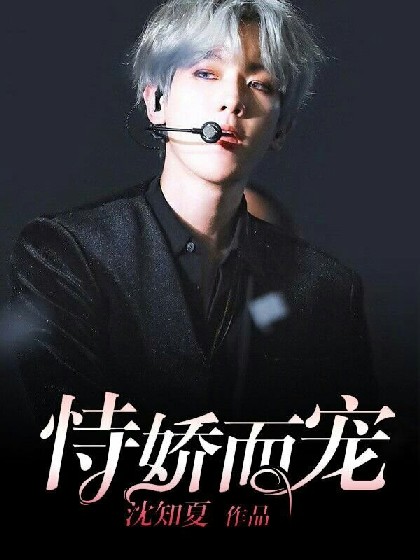入情
腊月岁寒,山木苍凉,一眼望去天际的蓝色竟然显得苍白无比,像是一位垂然的老者,苟延残喘着想要之成果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
屋外霜雪依旧,屋内借不来室外的天光,也显得暗沉的很。
啪的一声响动,惊到了屋内所有的人,人们皆是一愣,眼神齐齐的望向坐在议事堂主位上的孟鹤堂。
“哥?”
坐在孟鹤堂身边的陶阳有些小心翼翼的问道,如今的局势紧迫,眼看着孟鹤堂一日比一日变得忙碌沉默,众人的心里也都甚是担心。
孟鹤堂有些愣愣的看着地上茶杯的碎片,白瓷的杯子摔了个粉碎,好像打散了水中一轮月亮的倒影,不同的是,这一打破,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听到陶阳的轻唤,孟鹤堂好像稍微回过了点神来,他扶了下额头,丝毫还是有些恍惚的说道:
“没事儿,我没事儿,一会儿让人来打扫了吧。”
边说着,他却还是有些出神的微微低着头,喃喃自语道: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些心慌,这么久没见,也不知道张云雷那边怎么样了。”
他摇了摇头,好像是想要自己不去想其他的,赶快清醒起来。等他再次做好的时候,他的神情已经恢复了严肃。
“刚才说到哪儿了?”
“右护法,我们已经和本地的官府协议好了,暂时封闭高邑城门,守城对敌。只不过……”
说到这里,一旁的李九春稍微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担忧的神色,他的眉头皱起,像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后果。
“你接着说。”
得到了孟鹤堂的应允,李九春叹了一口气还是说了出来:
“只不过,封城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且不说我沧澜教的产业连接着周边一系列的城池地域。就说现下正值年关,正是百姓出城采办或者走亲串友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在过年的时候与家人分离,也没有人愿意一个年过的危机四伏。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百姓愿意配合是看在往日沧澜对他们不错的情分上,可若是因为沧澜让他们的佳节陷入危机,让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没有谁会真正情愿继续支持我们。不怕外敌强大,就怕堡垒…不攻自破。”
不得不说,他这一段话说的在理,历朝历代,更替的都是政权而非百姓,这两者间不过是简单的利益关系,互相成就,若是一方受到了威胁,另一方便会被排斥和厌恶。只不过,在这上千年的百姓与权力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最后都是前者。
孟鹤堂自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问题,他点点头说道:
“这问题,我也不是没想过。困守自然不是长久之计,但好在我们现下并非孤立无援,还是有人可以前来雪中送炭的。”
说着,孟鹤堂拿出了几封已经写好的信件,吩咐一个亲信手下道:
“你现在就去驿站,让传驿使者快马加鞭,把我的信送到各个分堂去,要求他们即刻前来支援。”
待那人领命接了信,孟鹤堂这才又向众人解释道:
“我沧澜毕竟分堂势力遍布北方,待到援兵到达,内外夹击,难不成还收拾不了悲喜宫的那群杂碎?”
他这话像是对众人说的,又像是对自己说的,也不知他是在说服众人,还是在说服自己。
做了这一番的定夺,孟鹤堂轻轻的摆了摆手道: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也不知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遭遇,大家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以便应对不时之需吧。”
众人应是,接着纷纷离开了议事堂。孟鹤堂看众人都走的差不多了,这次站起了身,准备离开。临走的时候,他又望了一眼那个被他失手摔碎的茶杯,那个茶杯的残骸静静的躺在那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显得格外的凄楚。
孟鹤堂的心里隐隐的有些不安,看着那个杯子更是觉得心中压抑的紧,他不知道那是这几日忙碌所致的错觉,还是此事真的是意有所指。他转过身,对着一旁的下人说道:
“把那里收拾了吧。”
孟鹤堂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亮了桌边的一盏烛火,借着那暖暖的光,开始处理堆叠无数的教务。不得不说,战争是一件麻烦的事,若不是真正经手了此事,孟鹤堂实在是不敢想象可以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琐事。
眼下的情况,逼着他事事谨慎,深谋远虑,以前的他可能是太过的自在逍遥,第一次面对这些,真的着实让他有些吃不消。他很累,特别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站在自己身后,他可以什么忙都不帮,就是站在那里就好,即使是这样,也能让他感受到分担和归属。
孟鹤堂不禁羡慕起张云雷来,那么个傲娇的性格脾气,却还真是可以让杨九郎对他死心塌地,不离不弃。
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张云雷越来越离不开杨九郎了,这是一种慰藉,不是单纯身体上的,而是在精神上就会给人一种归属感,告诉那人即便你十恶不赦丧尽天良,即便你身无分文苟延残喘,也还是会有一个人支持你接纳你,对你不离不弃。
只是可惜了,他孟鹤堂没有那个福分,他的身旁此时只有深沉的夜色和冷冰冰的空气,却没有一个像杨九郎一样的人。
“啧。”
孟鹤堂轻轻的啧了一声,他刚才想事情想得出神,没注意到自己手里的毛笔已经在纸上点出了一个巨大的墨点。
“我刚才想写什么来着?”
这一时间,孟鹤堂竟然望了自己那笔要干些什么了。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重新拿出了张纸,将其铺好在毡子上。
好像就没有多想,毛笔就已经在纸上留下了痕迹,开头几个字格外的显眼:
孟鹤堂诚送周九良收:
此念犹记当年,
此间还忆月前。
乘风万里书信送远,
无奈怎想戈壁当晚。
几多愁,
望君忧,
回环无法何人救。
霜雪寒腊独醉城头,
只把倾颓换回首。
路远遥,
西风啸,
为难可叹末路渺。
盼旧情折换,
君可临沧澜。
孟鹤堂看着自己似是无意写出的这首词,神情很是复杂。他拿起纸,轻轻的吹干了上边的墨迹。好像是犹豫了一下,孟鹤堂这才把这张纸折了起来,放进了一个信封之中。
他一边给信封封上口,一边小声的自言自语道:
“周九良,我孟鹤堂此生从来没求过什么人,今天,可算是在你这里立了头一遭了。”
烛火摇曳,映照在孟鹤堂的脸上,烛光的掩映下,孟鹤堂的眸子里闪耀着一点晶莹。这好像是他这么多天以来眼睛里第一次有如此灵动的光彩,不知道是因为烛光还是其他的什么。
“来人!”
孟鹤堂唤了一声,随即推门进来了一个下人。孟鹤堂把信交给那人说道:
“按照信上的地址,你现在启程,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信给我送到了,一定亲手交到那人手里。”
孟鹤堂说着,说道那人的时候,不自觉的加重了语气,心中狠狠的颤了一下。说实话,这封信完全出于他的私心,只不过打着求救的幌子。
与其说是沧澜教需要被拯救,倒不如说是他孟鹤堂需要被拯救。
他拿不准周九良接到信后会作何反应,也许结果会令人失望,不过既然他已经失望过这数不清的次数,即便是再多一次又能怎样呢?
其实他隐隐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如果还是得不到他想要的那个结果,那恐怕天意为之,他就应该考虑张云雷让他放手的建议了。
“是,属下这就去办!”
那下人接了命令,随即出了房间,当夜便策马扬鞭赶往了汉阳。一路上晓行夜宿,片刻不敢耽误,几天后,此人终于是到达了信上写的那个地址。
汉阳静安远世堂
自从孟鹤堂和张云雷离开了汉阳,周九良又回到了他的这个小药铺,继续过着他远离江湖的隐世生活。日子一天天的过,好像没什么不同,可是周九良自己却请出去的很,有什么东西已经在悄无声息之间改变了。
他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忘掉了曾经,回避了过往,让自己变得云淡风清。但是仅仅是不久前那一次偶然的相遇,便又在他平静的内心里溅起了一丝波澜。毕竟曾经生死相依,一同走过了那么多的千难万险,即便没有爱情,也总该是友情之上了。
感情从来就不是一件物品,想扔就扔,想找就可以找回来。他从来都不服从人的理智,忽然的出现,萦绕在心头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此时此刻,周九良和他店里的那个小伙计正在柜台前整理这草药,就在这时,那个负责送信的下人走了进来。
“请问,这里有位周九良先生吗?”
周九良停下手头的动作,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和往常一样平静的说道:
“正是在下,阁下有何事?”
那下人听闻正主在此,连忙上前先行一礼,随后才把书信呈上。
周九良接过信来打开一看,他的表情始终淡淡的,好似没有丝毫的起伏,可是实际上,他的心里却远远没有他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淡然。
“先生,您看?”
等了一会儿,那送信的下人见周九良始终没有反应,忍不住的便问了一句。周九良这才把信轻轻放在桌子上,悠悠的叹了一口气。他沉默的这段时间,其实心里一直在纠结和彷徨。他好不容易远离了那片境遇,若是此一遭去往沧澜,恐怕之前的努力便要前功尽弃了。他不是没有看出信中字里行间孟鹤堂的希冀,可是总归有句话说的好: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若是没有做承诺的勇气,便还是斩断这孽缘为好。
“我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医师罢了,江湖的这些,我不懂。”
最后,周九良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那么索性便让他断个干净。周九良一边说,一边拿起了柜台上放着的纸砚,提笔沾墨在纸上写到:
可叹垂帘暮雨,
无奈不赴期许。
恰时或逢秉烛当叙,
长路不适重山逆旅。
莫向思,
伶仃子,
萧然只盼旧情辞。
望君一解痴痴如此,
会吾意堪堪几字。
师凯旋,
无人叹,
佳音席酒伴余年。
诚祈远疆边,
天官佑沧澜。
待到写完最后一个字,周九良拿起纸轻轻的吹了吹,随后折起来交到了来人手里。
“带回去,给你们右护法。”
那人接了信,见周九良又重新和自己的小伙计整理起了药材,不禁忍不住问道:
“先生…您,不跟我一起回去?”
“我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医者,左右也是没什么用。你把我的信带回去,你们右护法自会明白。”
说完,周九良便不再去看那人了,那意思明白的很,慢走,我们送客了。待到来人无可奈何的离去,周九良这才长长的叹出了一口气来。那店里的小伙计是个心细的人,见了周九良如此,忍不住问道:
“先生,难不成,还在为那书信烦心?”
周九良看了他一眼,没再做过多的隐瞒,轻声说道:
“世间唯有情字难解分晓,又岂是一时半刻便可以斩断的?”
说完此句,周九良又是一阵的沉静,与此同时,那个小伙计却也没有错开他探寻的视线。周九良沉默了一时,好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一般,把笔一放,一掸袖子出了柜台:
“罢了,最后在帮他点力所能及的吧。”
说着,他披上了外袍,向着小伙计吩咐道:
“你看着店,我进一趟城,要是来不及,今晚可能就不回来了。”
说完,他便走出了远世堂,慢慢的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
汉阳城内,沧澜分堂,烧饼朱云峰正在书房里处理着一些七七八八的教案,时间接近年关,这个时候,总是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堂主,门外有人求见。”
烧饼从书桌后面抬起头来,有些不耐烦的问道:
“什么人?”
他的话音刚落,只听门扉声轻响,从屋外走进来了一个人,素衣整洁,正是周九良:
“怕是此时你事物多忙,我是不是打扰了?”
周九良看着烧饼说道。
“呦!怎么你有空来了?这平日里一起约出来喝酒都不愿意,今天是得闲?”
烧饼一见是周九良,急忙便起身从书桌后面绕了出来,满脸的喜色。周九良看他一副开心自在的样子不由得有些奇怪的皱起了眉头:
“你看来倒是不怎烦心?”
“烦什么?”
听了他这话,烧饼一愣,有些疑惑的问道:
“我除了年关杂七杂八的文书多一点,其他的,倒还真没什么。”
听烧饼这么说,周九良的眉头反而是皱的更紧了,他虽然久不在江湖,可还是敏感的便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沧澜教吃紧,孟鹤堂连他都寄了求助的信件,又怎会此时作为手握重兵的分堂主烧饼却一点也不像是知晓此事的样子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你不知道沧澜教的事儿?”
“什么事儿?”
烧饼更加的疑惑了,他完全跟不上周九良的思路,但是看对方的脸色越来越差,他也感觉到了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
“沧澜教遇袭,形势吃紧。”
周九良说道,声音沉闷的很,脸色也已经完全阴沉下来了。烧饼显然是吃了一惊,他愣愣的好久没缓过劲儿来,反应过来的第一秒,双手便握紧了周九良的肩头:
“你再说一遍?”
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知情,为什么竟然是早已退出江湖的周九良告诉他这个消息?
“就是你听到的那样,孟鹤堂给我寄了求助信,难道你没收到吗?”
周九良问道,语气严肃的很。烧饼一听,赶忙放开了周九良,转身慌忙的在桌案上翻找着什么,良久,他回过身对周九良道:
“没有,所有官道而来的信都从驿站取回来了,都在这里。”
“那怎么会……”
周九良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走上前去查看那些信件,果然,没有一封来自沧澜。
“不可能,给我送信的还只是个普通没走官道的下人,正常来说,通过驿站来的信都经了官方的手,应该会更快一点才对。”
周九良说着抬头直直望向烧饼的眼睛,此时,他只觉得心里那种不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所有的信都在这儿?你确定没弄错?”
他抓着桌子上那一堆的信件,沉声问道。
烧饼叫了下人来核实,一问之下,却还是没有遗漏的信件。此时此刻,连烧饼都感觉到了事情蹊跷,形式紧急了。周九良还算是冷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头脑飞速的运转,将送信人的流程仔仔细细的思考了一遍。
“去官府,去找郡守。”
忽然,周九良好像是想到了什么,招呼烧饼一声,向着门外快速的走去。
“官府?怎么?难道你……”
烧饼云里雾里的赶紧跟上去,一边有些摸不着头脑的问着,忽然,一道流星滑过他头脑中的阴霾,他的瞳孔骤然放大,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陡然而生。
“你怀疑是官府劫了沧澜教的信?”
“除此之外,你还有更好的解释吗?还有谁有权利可以随意的拿走沧澜教这么重要的信件?”
周九良说着,脚下更是加快了步伐:
“我有个不好的想法,希望,事情不会变的那么糟。”
他本来只是过来想嘱咐烧饼几句话,让他带给孟鹤堂的,可是居然让他发现了这么惊人的事实,若是他今天不来,那恐怕孟鹤堂永远都不会等来救兵了。
周九良思及此不禁是一阵阵的后怕,他虽然说着对孟鹤堂无恋人之情,可又怎能忍受他身处险境,刀口舔血呢?那么多年的情分了,怎么能说断就断,这些岂是他说了算的?
去官府的路上,烧饼随手叫上了一队的侍卫守军,这下声势浩大,还没进得郡守的门口,里面的人便已经知晓了一切了。
两人被拦在郡守府的大门之外,看门的卫兵看着乌央央的人群,尽量表现的和颜悦色道:
“几位,可是有什么事?我家郡守今日身体不适,还望……哎!您留步!您等一下!”
可惜了此二人现下已经是心急如焚,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心思与着卫兵多话,烧饼直接踹开了大门,带着一队人马鱼贯而入,直向着郡守的房间逼去。
到了门前,烧饼同样是临门一脚,只把那扇奢华无比的雕花木门踹了个粉碎。为首的两人进到室内,只见一人整装正向往屋后跑去。
“站住!”
烧饼疾走几步,一把便揪住了那人的后脖领子,直直的把人拖了回来,扔在地上。两人定睛一看,这不是汉阳的郡守又能是谁?
“听闻郡守卧病在床,今日一见还是挺精神的嘛。”
烧饼说着,俯视着地上的郡守,嘴上的语气平淡,脸上的表情却逐渐狰狞。
“朱堂主!这不巧了,在下的病刚好,刚说着起身转转呢,这不您就来了,呵呵,呵呵。”
那郡守一句话说的颠三倒四,他一边尴尬的笑着,一边就想手忙脚乱的从地上爬起来。可是就在此时,只听一声剑刃声响,随后便是寒光一道,汉阳郡守只觉得喉间一凉,反应过来才发现一把利剑已经抵上了自己的喉间。
烧饼也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低头,却只见自己腰间的佩剑却只剩下了一把剑鞘。
只见一旁的周九良不知何时已经拔剑在手,双眼愣愣的盯着地上的人,若是他的手轻轻一抖,那郡守的脖子恐怕就要见红了。
“这位…先生……您这是……”
郡守吓得连忙向后仰去,可是那剑锋随着他的动作移动,时刻逼迫在他的致命部位。
“你劫下的沧澜教的信呢?”
周九良冷声问道,他已经太久没有拔过剑了,此时他胸中有一股压抑不住的躁动,让他几乎没有耐心听完那人的解释边想结果他的性命。
若是说此前周九良对自己的猜测还无法百分之百的确定,可是在看了这郡守的反应之后,相信是只要不笨的人心中都已经有了定夺。
“什么信?我不知道啊!您…您先冷静…在下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汉阳郡守声音瑟瑟发抖,几乎听不清他的吐字。看见他如此冥顽不灵,周九良只是一声冷笑道:
“我的剑已经七八年没见过血了,别让你成为第一个它剑锋下的亡魂。”
他自从出世以后,便从来没有如此的极端过,他即发誓退出,便是再也不愿妄动那丝戾气。
烧饼比起还在克制的周九良显得更加没耐心一点,他抬脚在那郡守的膝盖上狠狠的一踩,只听咔吧的一声脆响,好像是里面的骨头应声而断。
“我没那么多时间,你再不说清楚,我就踩碎你的另一个膝盖!”
烧饼的脚下力道不减,在已然碎裂的膝盖上继续狠狠的研磨着。那郡守何曾吃过这种苦,嚎叫着求饶,一边尖叫,一边把所有的事实全盘拖出,毫无尊严,毫无骨气。
“朱堂主!朱堂主手下留情!不是我的主意,都是那玄正山庄的啊!他们联合了悲喜宫去攻打沧澜教,告诫我们所有的官府不许外传出任何沧澜的信件,封死全部的后路。最后沧澜所在的高邑官府联合城外悲喜宫人,内外夹击,要将沧澜一网打尽。都是他们的主意!我也是被逼的!
堂主!玄正山庄与官府一体,那么大的势力,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边疆小官怎么敢不照做啊!您手下留情啊!”
可是他这话非但没有引起烧饼和周九良的半分同情,反而让此二人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好像凝固了一般。阻截所有的信件,封死全部的后路,那岂不是说,孟鹤堂此时等不来任何一方的救兵和支援?就只能一人困守城中,直至城从内部瓦解,内鬼联合城外的敌军彻底毁掉他和他身后的沧澜?
那么此时,会不会已经为时已晚了呢?
周九良忽然想起了他的那封回信:莫向思,伶仃子,萧然只盼旧情辞。绝情决意,再无旧情。想到孟鹤堂可能会遭遇的一切,他拿剑的手都止不住的颤抖起来,他咬紧牙关,从牙缝中狠狠挤出几个字:
“信呢?”
汉阳郡守颤抖着双手在身上摩挲着,终于从怀里掏出来了一封已经皱了的信,一看,便是已经寄来有一段时间了。
周九良一把抢过那封信,展开一看,那的确是孟鹤堂的亲笔,写给烧饼的,不同于写给他的那首词那样婉约哀戚,这封信字字泣血,一看便是事态已经到了十万火急。孟鹤堂给他的那封信,更像是在一个人已然绝望之际最后存留的一丝温柔的希冀,再碎了,就真的没有了。
望君一解痴痴如此,会吾意堪堪几字。这是他在回信里写的:希望你别再痴情于无用的希望了,你看看我的信,我说的清楚,我们真的没有结果。
一股强烈的冷意席上周九良的心头,他不敢去想,孟鹤堂拿到那封回信,会是什么样子。
他咬着牙关,忽然狠狠一脚把那郡守踢出去了老远,没有再去理会他的哭嚎求饶,周九良急速的转身离去,一边对着烧饼有些失控的说道:
“整兵,马上出发去沧澜!城里有内鬼!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再晚,他真不敢想了……
德云社之lym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斗罗大陆2绝世唐门之霍雨浩黑化。
- 简介: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这是所谓的十几年的友谊吗?
- 1.2万字6年前
- 花千骨番外之重来一次
- 简介:花千骨在仙魔大战中被白子画一剑杀死了,奇怪的她竟然重生了《本文来自汤圆创作,请多多支持!》
- 1.8万字6年前
- 巴啦啦小魔仙之游蓝
- 简介:,,,,,
- 3.8万字5年前
- 问.灵
- 简介:本文背景:魏无羡被献舍重生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过是蓝忘机的一场梦……主cp:忘羡副cp:追凌先做好心理准备,此文几乎全篇刀子,慎入~本文原著:《魔道祖师》注:本文因为与原著同背景,会有部分原著内容,会在该章节处标明,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 24.4万字5年前
- 恃娇而宠
- 简介:三年前,沈瑜第一次见到了边伯贤.“你好好道歉,这事就过去了,嗯?”三年后,边伯贤看着狼狈不堪的沈瑜,满意的笑了笑“我要让你永远摆脱不了我。”“我希望你快乐。”“我希望你离开我之后无法快乐。”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失败,危险来打动你.我在如此想你.
- 2.4万字6年前
- 王者荣耀乔策恋
- 简介:本文甜文,不喜勿喷,说一下,情侣有,乔策,白昭,安亚,乔瑜
- 4.5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