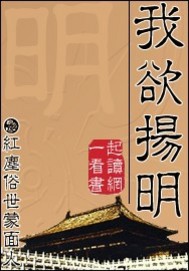第145章 城中内乱
朱汉旌得意地笑着说:“怕是可以攻城了吧?”
左右围着方百花、孙大哥、王胜、张松、吴路生等人都是点头,无人凑趣。这时候要是有人吹捧说道:“大帅英明神武,敌军疲惫不堪,正可以一鼓而下!”那该有多好?
无人凑趣,有人干活。
第三日午时初刻,抛石车、冲车、望楼车等大型工程机械在弩弓都阵列之后组装完毕。这是朱汉旌第一次见到大宋抛石车。
这种抛石车的机架两支柱间有固定横轴,上有与轴垂直的杠杆,可绕轴自由转动。杠杆短臂上固定着多根皮索,长臂末端有一个皮制弹袋用于盛放石弹。
朱汉旌看着十多个士兵在投石车短臂前站立,手里抓住皮索,另外有一个士兵搬运来一枚碗大的鹅卵石,放入长臂末端的弹袋中。有一个老兵站在抛石车旁边,猛吸气,大声呼喝道:“拉!”
十多个士兵奋力向下拉动皮索,长臂被拉得翘起来,将鹅卵石抛掷出去。
朱汉旌站在望楼车上,看碗口大的鹅卵石在空中划出一道黑色弧线,落在南城门口之前,又跳起来,弹了数次,滚到距离城墙脚还有数十步的距离。
城墙脚下密密麻麻列阵的乱军士兵大哗,人人都争相走避,露出一个很大的空当。
朱汉旌默默在心里说:“石弹小了点,距离也不够。”
那个老兵也不泄气,喝令道:“下次,用力整齐些!把你们在娘们身上的气力都使出来!”
在士卒哄笑中,抛石车又一次装弹,发射。这次士兵拉动皮索的气力也大了些,整齐了些,石弹抛得更远一些,落点仍然距离城墙有数十步。
城墙下乱军大哗,开始有人要逃,裹着黑布头巾的乱军军官奋力约束,这才把队形勉强约束住。
那个指挥抛石车的老兵请求将抛石车推向前,朱汉旌允了。弓箭都大都头王胜将弩弓手向左右分开,让出一条通道,让这部抛石车前出到弩弓都前面。
又是一次抛射,这次石弹落在城墙上,在夯土的睦州城墙砸出来一个小小凹坑。石弹弹落下来,没有砸中任何一个守军,可是又在乱军中引发一阵大哗。
从午时初刻到未时三刻,官军唯一的抛石车不断抛射碗口大的石弹,在城墙上不断砸出浅浅的凹坑,对城墙的伤害极其有限。除了偶尔有几次石弹飞过城墙,落入城中,多数时候,石弹只能砸到城墙边上。
可城墙下的乱军不干了。
呆立城墙下,挨饿挨冻又挨打,这些倒霉被派出去的一千乱军纷纷叫嚷着要回城。朱汉旌在望楼车上看到,挥动红旗,喝令下面阵列做出佯攻姿态。
弩弓都、刀枪都阵列向前逼近了三十步,逼得睦州守军不敢开门。城头上有军官严令不许撤回,城墙下守军戟指大骂,城上城下纷乱得不行。突然有人大哗:“跑了,跑了!免得在城下受死!”这个士卒说完,丢下手中简陋的木棍,扯掉红色头巾,撒腿往官军大阵方向跑过去。
城头上有军官看到逃兵,大叫:“射箭,射箭,射死他!”就有十多个弓手纷纷向下射箭。这个乱兵已经饿得有气无力,跑得很慢,一支羽箭毫不困难地追上他,一箭射倒。
然而更多逃兵已经绝望,再也不肯留在城墙下等死,不顾城头零星羽箭,纷乱地朝着官军阵营跑过去,一路扯掉头巾,丢下兵器,口中乱嚷:“别杀俺啊,俺是来受招安的!”
朱汉旌在望楼上,喝令军阵分开一条通路,让这伙乱兵逃入阵中,自然有后军将其收容。
只花了两刻钟时间,城墙下一千守军逃了一个精光,本来还有几个军官还不敢逃走,可看到自己的士兵逃光了,回去也是军法处置,干脆自己也撒开脚丫逃了。
朱汉旌在城下,围困三天,收容一千降军。
城头上士气更加低落,连在城头上张望的士卒都少了很多。
朱汉旌在这些投降的士兵中挑选出来几十个大嗓门的,吃饱之后,举着木盾,轮流靠近城下呼叫同乡同村亲友。
“兀那吴老四!俺们吃饱了!有米有咸菜!不再挨饿受冻!你也赶快弃了兵器,来招安吧!官兵有粮有饷,从不拖欠!要是能把方腊首级割来,便是一百贯的犒赏!听到了无?”
“兀那刘家十一!割不到方腊狗头,割了你的上官狗头!一个都头,也是一贯钱!”
“兀那姓卞的小九!看在同族同宗才告诉你!快快带人逃过来!你当那个都头,管了七八十个人,什么时候让人割了脑袋卖钱招安,也不晓得!不如逃过来吧!带一个兵来,就是五十文赏钱!你带八十个人来,莫不是有四千文钱?足够你好好买几亩地!大乱过后,地价不足往日的十分之一!”
“兀那韩老七!你的婆娘让方腊抢走了!你被裹挟从军!官军都知道!赶紧反正!杀了上官,提着脑袋来投奔!早点动手,莫要让人抢了功劳!官军平了方腊,你那被抢的婆娘才能回来,你还犹豫什么?”
“兀那白斯文!你抢了多少婆娘?我家婆娘就是被你抢走的!被他抢走婆娘的人都听着!杀了白斯文那奸夫,杀了他!报仇雪恨!还能换钱!一个都头的首级!换一贯钱!白斯文手下有八九十个人,都不眼馋这一贯钱么?”
“兀那肖大郎,还记得都头踢翻你的饭么?你的父母兄弟让都头杀了,逼迫你从军,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何况你的婆娘还被强污了!还在等什么?杀了都头!报仇!换一贯钱!”
“兀那张二!你不是在伙房帮厨么?随便点了厨房,烧了薪碳,造就一场混乱,便是好大的功劳,起码有百文赏钱!还报了强抢婆娘的仇!”
“兀那伍家小六!你长得猴子似的!会上墙上树!你把那粮库烧了!算你十贯钱!纯铜足陌,却不是省陌钱!”
“兀那王小八!你还在伪皇宫当厨子不是?下点砒霜!一次药杀方腊全家,却是有好几百贯赏钱!”
……
诸如此类的说辞,一段一段,都是金融骗子金德编出来的。大部分真,小部分假。真假混合!在城下喊出来,喊得城头上人心浮动。听得城头上的士兵人人想要逃,听得城头上的乱军头领恼怒不已。城外如此煽动士兵,怕不是要兵变么?于是乱军头领都要求加强巡视,不断弹压,自己不断走动,看看哪个士兵有异常,批头盖脸一鞭子打过去。这下午到黄昏半日,不知道有多少士兵挨了打。
只这半日,城头上便是人心浮动。而到了傍晚,经过士卒与送饭厨子口耳相传,这些煽动话语又传到了城中后方,传给了伙夫、帮厨、杂务、仓管,通过这些人传到后方士卒,传着传着,全城人心骚动。方腊大军粗创,未能好好整合,基本上就是谁去裹挟、强征多少人,就给一个官衔。这样的做法好处是如同滚雪球一般快速扩大,越滚越大,短短时间可以裹挟上百万人从军。这样做的坏处就是组织结构松散,干部队伍不稳定,人心浮动,组织纪律性很差。依靠打胜仗与抢掠维持士气与组织。一旦遭遇挫折,便如滚汤泼雪一般,冰消瓦解了。
可恨的是城外的大嗓门彻夜嘶吼。到了夜间,官军还做出了好些个铜皮喇叭,吼叫起来,声音响亮。这些煽动话语越过城头,吼叫得城墙内猬集待命的士兵人心浮动,交头接耳。
士兵们多数是被裹挟来的,其中不少人还被抢走婆娘,抢走米粮,烧了房子,不得不从军。他们担心在困守废墟里的老父母,牵挂被抢走的婆娘,可是要他们就此杀了头领造反夺军受招安,他们也不敢。一夜城外嘶吼,城内士卒心中都是凄然彷徨。有人哭泣起来,然后就是一群人哭泣起来,最后满城皆哭,从抽泣变成嚎啕,很快成为歇斯底里的咒骂。
有都头带着亲兵来约束,皮鞭挥舞,挨个儿打。起初那些士兵还抱头躲避,哭泣着挨打,后来打得狠了,有士兵愤然反抗,揪住了鞭子怒问道:“好你个都头!抢我米粮禽畜,胁迫我从军,你还想杀我?”
那个都头仗着身边还有十多个亲兵,喝骂道:“徐老九,你敢造反?”喝骂之中,就有亲兵拔出杂七杂八的各色佩刀,围了过来。
那个名叫徐老九的乱军军汉气愤道:“难不成跟着你不是造反么?你们说造了反,杀贪官,吃粮饷,可你却占了俺的婆娘,抢了俺的米粮禽畜!”徐老九指着周围的乱军军汉,问道:“哪个当兵的没有被你抢过?说好了抢来的米粮都是自己的,不料都让你和亲兵独占了!这兵,俺不当了!”
这徐老九顺手夺过旁边一人手中的木棍,怒喝道:“反正过不下去了!与其兵败身死,不如杀了都头,换钱受招安!”
这个叫做杜留的都头看那身高力大的徐老九操起一条棍子,吓得向后一缩,摆手说道:“亲兵!亲兵!上!打杀了这反贼!”
左右亲兵听令,吆喝着围上去。这处兵营是占据了城墙内一处酒肆,这些乱军士兵就在这里蜗居,将桌子椅子拼凑起来做大通铺睡觉。此时还有一片厅堂空地,这就便宜了徐老九。他用的是一条硬木棍子,在厅堂里面比短刀好使唤,当下一通乱舞,就打翻了好几个亲兵。其它亲兵看着形势不妙,畏缩不前。
这个徐老九还不忘记大喝:“都上啊!不然就全让都头给杀了!”
都头看着徐老九威猛不可敌,情急生计,匆忙叫嚷道:“只杀徐老九一个,不及他人!”
这群乱军士兵个性懦弱,也让都头给欺负惯了,都头又是出言安抚“不及他人”,于是紧要关头,无一人敢于反抗,就缩在墙角,眼睁睁地看着徐老九一个人苦战。
徐老九豁出全力,苦战一盏茶功夫,无人相助,他以一己之力打翻十来个亲兵,也用尽了气力,脚下一踉跄,拄着硬木棒子才没有摔倒。
这个叫做杜留的都头本来已经吓得退缩到门口,看到徐老九只剩下喘气了,不由得壮起胆子,抽出佩刀,狞笑着兜头劈过去,口中叫道:“砍死你!”
徐老九想要躲避,无奈已经无力,硬生生地被他一刀看在头上,鲜血迸溅,当即倒地不起。
都头杜留狞笑着将徐老九乱刀剁碎,口中喊道:“谁敢造反!就是这个下场!”
满屋子血腥味弥漫,而其他士卒都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无人敢于反抗。
这一夜,城内多少小规模的反抗被扑灭,时不时有惨叫响彻夜空,凄厉的呼号弥漫不散。
宋时儿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大明帝国
- 简介:当年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本书数字版权由“当当”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04.0万字6年前
- 瑾世子的俏医妻
- 简介:雨夜赶路,中医学界的天才离柯在雷雨之夜人车坠崖,魂穿异世,灵魂进入被追杀而坠崖的十三岁女娃的体内。三年学医,出断魂谷,追查凶手,偶遇冰块男,立马被坑,再遇只是,为寻得对方的道歉,紧随其后。疑云一步一步的解开,感情一点一点的加深,彼此手牵手,共赴磨难。而这一路,离柯和欧阳瑾有着怎样的奇遇?看离柯如何在异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QQ小基地:(373985675)欢迎你们的加入。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89.8万字6年前
- 我欲扬明
- 简介:当了皇帝,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铮铮直臣,为何反对强国富民的新政?权相阉宦,为何却成为改革的推动者?正气与私欲的激烈交锋,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残酷斗争,是人改变了历史,还是历史改变了人?附身酒色昏君,重振大明河山,一切都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450.6万字6年前
- 新闯王
- 简介:你们的穿越都是为将为相,我的穿越却成了流民,命运何其不公?本想置身事外,但人和事推动着猪脚,一步步无奈加入到这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之中.主角也不是全能人物,敌人也不是猪一样的愚蠢.没有一帆风顺,只有不断跌倒爬起.这是一个斗智斗勇,忠诚与背叛纠结的热血传奇故事,给大家一个全新思路和全新感觉的明末天下。“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63.2万字5年前
- 改变历史的12大伟人
- 简介:一家飞机从台北飞到北京,可是飞机失联了,然后(她)她们都穿越到了1880年的清王朝
- 6.4万字5年前
- 宦海弄潮
- 一起枕边人与结拜弟兄精心炮制的车祸一次绝望中做出的无奈抉择一个好人的消亡一代枭雄的崛起跨越千年,从矜贫救厄的慈善家,到不择手段的陈亲王,命运的洗礼,亦是攀登的阶梯波诡云谲的宦海,处尊居显的权臣,笑里藏刀的皇亲,算无遗策的谋士人生在世,如处荆棘,不做天上鹰,便为笼中雀尔虞我诈,机关算尽,宁可万骨枯,终成一将功
- 1.5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