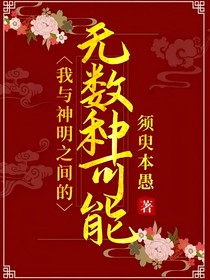加速、意识形态,智能和宗教(一)
Nick Land访谈:加速,意识形态,智能和宗教
□贾斯汀·墨菲:你基本上是主要的思想家之一,我可以说是主要的思想家,我们可以称之为Accelerationism思想学派。Accelerationism是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历史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几乎混淆了我们思考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所有传统概念。这只是为那些不知道我们将要谈论什么的人准备的,这基本上是你所熟知的思想流派,所以也许在我们继续之前(这是我简短的“电梯游说”),你能补充点什么吗?如果有人在街上走到你面前问你“这Accelerationism总体是什么?”在我刚才说的基础上,你还有什么要点要补充吗?
■N:我们将要进行这个对话,所以,你知道,尝试和预测可能是一个错误,我认为当我们开始谈论它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Accelerationism的各个维度。就我自己的参与而言,我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指导术语是控制论。加速论者的基本论点是,现代性是由正反馈过程而非负反馈过程主导的,而控制论的第一波理论——始终将负稳态反馈规范化,将正反馈病态化——因此已经自我淘汰。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立场,考虑到-正如你所说-现代进程的基本加速趋势,最极端的是在技术和经济层面。这就是“现成的”概念词汇,我认为,至少最初是这样的,但它本身是非常动态的。我们已经看到,一系列不同的系统和职权范围被卷入了这场Accelerationism的对话。
□贾斯汀·墨菲:我一直非常好奇你早期的工作和你现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之间的关系。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很多早期作品,都倾向于采用一种相当激进甚至是解放的政治基调,我想这样说是公正的,这是一种非常反叛的安那其主义,有很多女权主义的内涵,而且很明显风格非常赛博朋克。这一切都是关于在新的数字语境下构想的反叛企划。像“入侵macropod”和利用你所谓的“人类安全系统”中的小故障之类的概念……你谈到了“k-war”,我把它理解为革命游击战,但是在社会编码的层面上,对抗你称之为人类安全保卫系统的巨大某物。当时你甚至对更具幻想性的想法感兴趣,比如“新·利穆里亚时间战争”,你会觉得你当时的立场似乎是,这些Accelerationism的见解可能会让反社会的分子或团体根本地篡改或者说hack掉社会现实,以一种现状机构无法防御的方式,就一种迷醉政治的感觉。所以很多对你的作品和思想感兴趣的人,都是通过这些早期的文本接触到你的,我想我们都知道,很明显,从那以后,你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我认为不清楚的是,你的思想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或者只是如何理解那些早期令人兴奋的、解放政治的音调和Accelerationism的政治观,其与你目前的观点之间的轨迹,等等。所以在你开始讨论你现在的观点之前,在你开始思考你今天如何看待这些事情之前,我很好奇你是否能在精神上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你开始理论化所有这些激进的想法时。对你来说,这种倾向的最初破碎是什么?具体是?在90年代,你的观点中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见解、问题或非常态,让你意识到所有这些激进的解放思想都行不通,你会如何解释?
■N:事件是一波接一波的。波动是其中的关键。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CCRU参与掀起了一股极其激动人心的浪潮。你知道,互联网基本上是在那些年降临的,在文化、技术和经济方面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非常令人兴奋,它们携带着这种Accelerationism的潮流,使它非常,立即对人们来说是可信的和有说服力的。也许有些离谱,但绝对令人信服。随之而来的——我不想给出具体的日期,真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度幻灭的纪元。我称之为Facebook时代,显然,对于任何一个从德勒兹和加塔利毕业的人来说,所谓的“Facebook”成为赛博空间的统治性代表几乎就是,你知道,一件可笑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笑)。
我对此的反应是如此的彻底,持久的厌恶,以至于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种延宕不绝的,深处层垒的暴躁情绪被添加到这一点上。但我不认为这只是个人问题。我认为Accelerationism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日食…
□贾斯汀·墨菲: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的本质——这是我今天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之一——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经验的复杂方法来理解社会群体倾向于按照意识形态维度划分,诸多维度的数量,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它非常迷人和重要,因为我认为这些界定了当代大量疯狂和困惑的轨迹……在我看来,听你描述你自己的轨迹——这听起来就像是你在支持意识形态的所谓马蹄形理论,即生态位上的激进左翼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必然变成右翼?这似乎已经融入了你所说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式Accelerationism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反抗资本主义的真道是,自己变得如此资本主义以至于资本主义本义无法处理它?你是这么看的吗?
■N: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建议,在提出这个建议时触及了一个非常迷人和复杂的领域。
□贾斯汀·墨菲:对你来说,这有什么问题?
■N:在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有一种讨论结构,显然和你的观点紧密相关,它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涉身于这种诡秘狡猾的策略,我将把他们作为我们所涉及的事情的缩影),这种策略导致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Accelerationism诞生之初就一直困扰着,也就是“作为一种社会进程,这究竟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的问题——我们看到人们后来在不同阶段探索这个问题。最初的左派观点与我们后来所说的“左翼加速主义”完全不同。这几乎接近于列宁所说的“越糟越好”。对它的理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推动的,他们身上的Accelerationism思潮,认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将其加速到极限。没有什么其他的战略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马蹄铁来模拟吗?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被定义为资本的凶猛对手的极端右翼分子们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交汇点吗?是的,我承认,在这种框架下,这不是不可信的,也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些有趣的交叉。显然,有一个人处于这一问题的边缘,并引起了许多在Accelerationism相关领域工作的人的极大兴趣,他被称为Damn Jehu(如果我的发音正确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我见过的最绝对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的反资本主义啊无产阶级革命啊经济最终决定啊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他的分析和Accelerationism潮流之间有巨大的共鸣,可以被视为绝对的,冒犯性的,明目张胆的右翼取向。在你所说的背后有一些严肃的根据,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我必须把我的第四点放在桌面上,这将反弹到这个问题上,右翼Accelerationism者的基本承诺(它为后来的各种事情提供了支持,但肯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生或形成了):事实上的保守主义的社会力量——所有被称为“反动”的东西——是政治左派。政治左派本质上就是被架构起来反对将进程加速的律令的。
根据左派的这一界定,我可以在我不在置身于学术界设定的特定战略语境下这么说,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界,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霸权结构——将Accelerationism呈现为一个左派项目完全只是一种误导性的,Accelerationism与左派的本性如此不相容,当然,只有出自某种策略性的考虑我才会说自己是左派,但是,当你不再有压力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Accelerationism会对左翼保持某种亲近感或感情,当它有能力对形势告白,就会仅仅说“看,左翼是逆动于Accelerationism进程的,它是对立面”……这就是我说它不是真正的马蹄铁的地方,如果你继续用这一概念术语来定义左翼,那它就会失去任何实际的社会学意义。
□贾斯汀·墨菲:是不是说你认为左派和右派的划分都是肤浅的、战略性的、社会性的、摩尔式的结构,它们实际上是相互强化的偏执狂式的简化,试图解决经济加速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焦虑。如果你过于严肃地对待其中的任何一方,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结论突然陷入另一边,但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有意义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都是妄想或战略需要上的简化,最终都是当代社会(煽动人们对立)的虚假轨道,或者类似的东西?
■N:我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个术语,对于任何像你这样痴迷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完全理解为什么人们对这种(分类学)语言感到不满,说“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语言”或“这种术语不再有用”,但我感觉它有一种极端的弹性。我不认为我们会停止谈论左右的概念。它总是会回来,我称之为主要的政治维度,有一个基本的维度化框架,有左右两极差异,每个人在徘徊和模糊之后都会回到这个维度中。各种意识形态潮流本身都有战略利益,要么搅浑水,要么意图让人们重新思考他们的表达。
但最后,人们回归到意识形态可能性的基本维度,我认为这是最清楚地抓住Accelerationism倾向的一个维度。在右翼一端是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安那其资本主义的承诺,最大限度地放松技术和经济过程的管制。而在另一端是一群分子,他们以各种方式寻求——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我会说“阻碍”、“阻碍”、“约束”之类的词,但我意识到这只是我展示的右翼偏见,还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来调节或控制过程或使它人类化。我不会试图给自己做一个足够复杂的意识形态图灵测试来试着得到正确的答案,你知道吗?
但我不认为有任何真正的……并不是真的有问题,这些冲动中哪一种在起作用,我认为在这个维度上所谓的左翼Accelerationism之所以左,我的意思是,(能够被清晰辨别为)左的,是因为它基本上处于对资本主义进程的深刻怀疑的立场。它是Accelerationism者,只有当它认为有其他的——我会说是神奇的——将位于现代性的基本发动机之外某个地方的加速的动力来源,它们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你把实际的加速马达扔进(左翼政治的老套实践的)垃圾堆时,仍保有以某种方式加速。我想这是左。
左翼Accelerationism以一种强力的方式左倾,每个人都会认识到,他们实际上肯定是真正的左翼分子,他们不是在玩那样的游戏,他们催化过程,很明显,一旦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形成右翼反对派,因为他们已经是主要的政治维度。它们在它的左极,它们与定义同一光谱右极的东西对立。
a
□贾斯汀·墨菲:听起来你好像说德勒兹和加塔利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可能是在左派的环境下写作,他们可能有一些左派的内涵,但他们的项目的核心不是左派,因为……你认为左派的立场基本上是试图减缓加速器的吗?
■N:是的,我认为他们项目是反左翼的,但却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内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阴险的策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很容易从内部被颠覆,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资本主义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方面。一旦你这样做了,你就是在描述加速的动力源,一旦你更进一步,像德勒兹和加塔利做的,显然马克思有时也做,实际上接受了这种马达所生产的推动力,你就到了那一步。我是说,你已经越界了。
□贾斯汀·墨菲:好的。我认为这澄清了一些事情。这很有趣,因为你还说你认为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中有周期性的趋势,似乎是指在某些时候和地方,为了追求激进的批判性哲学,你会倾向于发现自己是左派,但在其他时候和地方,可能更多的是右翼的表现。是这个意思吗?
■N:是的。没有比这更清晰的了。但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不会对此做出教条的回应。当然。但我认为这场对话可以沿着一个庞大的、极其有趣的思路展开,完全由你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来引导,也就是,“批判的历史是否经历了这些奇怪的意识形态振荡的过程?”我认为确实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一点。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真正严格而清晰地揭示这种模式,但我绝对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大理论力量的核心,绝对是一种严格的康德式的,技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暗示,我认为,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作品中,这是翻转的,但也很复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只是发掘了马克思已经操作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的理论,甚至没有脱离他的批判结构,他们只是把马克思的理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所以也许你想说的是有一种地下的右翼暗示;甚至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刻,作为它的绝对对立面。
□贾斯汀·墨菲:那么,如此怎么样?如果我们跳出意识形态的问题,让我问你一个包含其中的,但除却了意识形态束缚的问题。具体来说,我想稍微回顾一下你们在90年代花了很多时间来建立理论的所有这些概念和想法。有很多非常具体的机制或策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在早期的作品中提出了理论,人们基本上可以重新设计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方式,我之前提到过其中一些,就不赘述了。
但我想问你的是,你的社会经验模型是否发生了改变以至于那些重新设计社会现实的战术思想你认为它们不再起作用了?或者你认为它们有效是错误的?或者仅仅是那些人类改变社会现实的战术能力,也许你会坚持认为这些想法仍然经验地描述了对人们来说可以获得的真实可能性但它们只是因为特殊的原因而没有被追求,还是什么?
■N: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都很有意思。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我只是重复一下你的语言:各种类型的策略潜力。但我只是想把它们从任何主体化的归因中抽象出来,因为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另一方面,会让事情变得复杂。现在,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谈论的是人类主义的问题,在更广泛的(一般的)意义上。人是谁?谁在干人事?
在你提出这个问题的表述中,这很像个体或集体,以一种相对传统的方式,被构想为能动者(agent),利用这些时机和策略,因此将其作为工具。这里有一个清晰的目的论结构。因此,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能动者的层级,你会有一个政治领路先锋的概念,他们的个人或集体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他们的工具、设备或资源。
第二个方面显然要复杂得多,尽管第一个方面(策略机会)……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绝对没有必要退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整个Facebook……Facebook的衰退是负面的,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白炽化的、技术和经济可能性的新阶段,这是由互联网这个基本的动态矢量(话语)所驱动的。现在的基本社会历史境况与20世纪90年代的任何情况一样激动人心。完完全全。
我想说的是,这些区块链技术,我的意思是,它们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某种极其抽象的哲学意义上被构想的,每个人都认为(谁在关注这些问题),每个人都能看到互联网将要做的是生产出这些分散式结构,这些结构逃避了那种既定(建制化)的治理结构,在某种反叛的意义上,是激进非政治的。你回顾这些早期的赛博朋克和数字安那其主义者的作品——蒂姆·梅,像这样的人——他们抓住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以及将会做什么,将意味着什么,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看到了这些,然后他们失去了这种视景……互联网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极其可悲的机会,让这种自恋内爆回最可悲的主体性形式。
之后在过去的几年里,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规模的令人兴奋的进程的复兴,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确定它的确切日期的。
这说起来很简单。我完全没有对这些进程产生怀疑。但我一直抱有怀疑的是所谓的使用这些进程的能动性的结构。我很抱歉,如果我又回到了你希望避免的意识形态的术语,我觉得与左翼绝对的距离是,我认为它预设了个巨大的神话,一个巨大的,人类主义的神话,关于这些人类主体(agent)的事实,他们在最后的分析中是可以信任的,有良好的政治倾向性,我们应该听他们的,我们应该相信他们的政治判断和直觉,所有这些技术-经济资源本质地属于一种位于其政治方案之下的目的论上的从属化状态。
所以有了“实践至上”,资本主义(笑)……总结一下,作为技术和经济的物质性在原则上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在有所谓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镇压之前,你就已经有了理论上的镇压,因为你认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包,可以放在各种各样的人类主体手中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正如你已经说过的,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我是说,这一切,都是人类安保系统!(笑。我不相信人类安保系统,它不是我的朋友……我不想给它赋权。我不是…为它当拉拉队。我不希望它以任何方式改进自己的掌控力(优势地位)。你知道,我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它的玩具或工具。我和它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
□贾斯汀·墨菲:所以基本上,你在90年代思考的所有东西,都带有非常左翼气息,或者是非常解放的动机、动力或内涵——或者我不知道你到底想怎么称呼它们——但是你在90年代理论化的这些看起来很解放的观念……你实际上根本没有否认它们。有趣的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当我们走出Web 1.0或2.0的低谷时,你实际上认为它们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这很有趣。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白梓萱与王静
- “东关小学就像那五只小羊一样,快乐,幸福,美丽”“只有露西,并不像只小羊”“东关小学又是一个美丽团结的羊村”“善良团结”“有时候村里也可能混......
- 0.2万字6个月前
- 师妹修仙:笑闹青云间
- 本以为修仙之路严肃艰辛,可谁能想到竟有这么一位沙雕师妹,将整个修仙界搅得欢笑不断!看她如何在青云间摸爬滚打,凭借自己的无厘头和独特魅力,闯出......
- 2.2万字4个月前
- 我与神明之间的无数种可能
- 【双向暗恋+一见钟情】都说神明普度天下,潞鸢却不赞同。初入九重天,潞鸢带着灭族之痛,一腔怒火,此生只为手刃仇人与神明。再入九重天,他带着身后......
- 10.8万字3个月前
- 长夜的消散
- 白色的风筝也要独属于它的夜晚
- 0.2万字3个月前
- 星星在闪耀时,是我在对你说话
- 这是一本虐文,不是很虐,最后除了女二都死了
- 0.1万字2个月前
- 特种娇妻不好惹
- 一个平平无奇却总认为自己特别的女子遇上一个兵哥一段奇缘的故事(书中修改中)
- 8.7万字6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