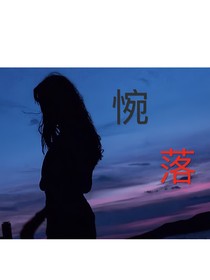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理论(三)
3. 现代性与基督教
4.
《近代的正当性》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的自恃(self-reliance)或(如布鲁门伯格所说的)“人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这一近代主题的起源和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变得如此专注于安全和生存,对缺乏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对获取一切种类的手段(资本、技术、对世界的机械论解释)都乐此不疲——总之,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世俗”,如此不愿依从于(就像前人那样)一种宇宙秩序、一种神意或被许诺在来世得到拯救?
在讨论布鲁门伯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如果现代性是以这种方式描述的,那么哥白尼本人就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人(尽管他被认为在近代的自我形象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自笛卡儿和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看来,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世界”——是原则上不可接受的,这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一直被那些想让哥白尼本人充当标志近代开端的革命者的人所忽视的原因。哥白尼极其幸福地不晓得,自己后来将被称颂(和谴责)为“把人从中心移开”,听任其自生自灭。
关于近代的“自我肯定”源于何处,现在通常的回答是,它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的、正常的和理性的态度,一旦诸如神话、独断论和偏见等障碍——以及像宇宙的和基督教的神意以及拯救的许诺等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被驱除干净,这种态度就会自行肯定自身。至于为什么这些“障碍”会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看法。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和古代寻找现代性的“征兆”(许多人都就此做过不少努力)当然并不解决问题。自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以来,这种对现代性自身的天真的无知已经引发了这样一种怀疑,即现代性实际上是否代表着一种与某种更加伟大的、更为一致的生存模式(时常被等同于基督教、神话、宇宙秩序等等)的可悲的决裂。
正如《近代的正当性》的标题所暗示的,这并不是布鲁门伯格的态度。他在那本书中倾尽全力来反驳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近代概念实际上是中世纪和基督教的原初概念的“世俗化”版本,因而是不正当的。但他也不接受通常的笛卡儿/启蒙运动/实证主义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形象,即认为它完全是“正常的”和没有问题的。他的做法是对“现代性源自何处”进行一种全面的分析,而没有把它当作其它某种东西的一个转变后的版本,或者是某种始终就在那里的东西(但被其它事物遮掩起来了),他明确指出它不是“突然间”发生的。简而言之,布鲁门伯格把现代性说成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个问题隐含在中世纪晚期关于上帝、人和世界的整个思想状态中。正是这个问题使得现代性在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刻成为适当的,而在较早的时期,由于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它尚未浮现出来),现代性也就隐而不现。
布鲁门伯格给这个问题定出的标题是“神学决定论”。它指的是中世纪晚期对于上帝的全能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隐匿的上帝”(hidden God)的观念的强调,对于这样一个上帝,我们不能指望以任何方式去理解。在神学中,这些观念导致了人甚至在选择信仰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就像任何其它事物一样,这也是由上帝随意地、无法理解地赋予或拒绝赋予的。这种处境的任意性往往通过灵魂或被拯救或被毁灭的永恒“命定论”的观念表达出来。在哲学中,这种想法导致了教会对亚里士多德证明世界独一无二和永恒存在的谴责(巴黎,1277年),后来又导致了唯名论否认共相的实在性。这些源于希腊的学说被怀疑给绝对神圣的权威所要求的全能设置了界限。然而结果却是,正像人的信仰和拯救被置于一个完全无法知晓的上帝手中一样,世界也是如此,它丧失了古典哲学和盛期经院哲学中的一切使之可以理解和可以依赖的特征。“神意”现在只是作为上帝为选民的预备才有意义,而不是针对人类或一般意义上的世界。这一处境(在这个为神而非“为人”创造的世界中,人是不可能自在的,但是从中逃离的任何方法都完全超出其能力之外)代表着人的自我牺牲的极致,它不可能被无限期地忍受下去。事实上,从宗教改革运动到宗教战争,在与这些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之后,许多欧洲人多多少少有意识地、实心实意地把神学决定论的人的自我牺牲替换成了近代的“人的自我肯定”,人们决定看看“即使没有上帝”,他们可以把世界解释成什么样。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公理必定就是:我们无法认识现象的目的和“目的因”(因为要知道它们,就需要知道并依赖于上帝的意志),而只能认识其“动力因”,通过它们,我们发现我们可以造出同样的现象。
至于中世纪晚期是如何发生这种转变的,布鲁门伯格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述。非常简要地说:关于神的全能和命定论的神学在公元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的晚期著作中被首次明确提出。布鲁门伯格写道,“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多种方式重复了奥古斯丁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这条道路呢?又是通过一个问题,即如何“把创造之神和拯救之神统一在同一个体系中”。对于基督迫近的再临以及世界终结的期待已经把所有重负都放在了“拯救之神”上。由于这种期待越来越令人失望,于是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显然将留驻其中)的神就再次成了一个问题。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声称,这些神之间的对立是因为:他们是彼此对抗的不同的神。布鲁门伯格称,这一似乎有理的对于困境的解释是教父神学——在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和原罪(使人对世界的悲惨状况负责)的学说中,后又在神的自由意志、全能和命定论的相关观念中达到顶峰——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但是为达此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却酿就了一个问题,即“绝对原理对于宇宙堕落(全部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它)的责任终究还是通过命定论的观念被间接地重新引入了,因为这种罪连同其一般后果……只有万物原初的基础才可能负责。”这就是布鲁门伯格把近代描述为“对诺斯替主义的再次克服”的意思。这一论题预设,“在中世纪开始时对诺斯替主义的第一次克服是不成功的。”
5. 哥白尼与基督教:“哥白尼之可能性的开启”
6.
显然,作为一个哲学家,持有单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哥白尼没有料到,也无法逃脱近代的“自我肯定”对于目的论的无情批判。他也没有料到它的其他那些特征性主题:自我保存、缺乏、技术(和实验)的重要性、方法以及对方法的怀疑或批判。他的立场所预设的实在在本体论上的统一性预示了伽利略和笛卡儿对于物理世界的同质的数学化,但这种统一性却从未被明确地讲清楚过。尽管我们追溯既往,对他进行英雄化,尽管他的著作对于近代意识的直接可辨的影响也许要比所有“自我肯定”的哲学家加在一起还要大,但哥白尼实际明确表达的哲学命题却使他的哲学立场(作为一段“过渡中的插曲”)并不属于近代。
自十九世纪以来,许多历史研究都倾向于把现代性的起源或最早的迹象一直追溯到被十八世纪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布鲁门伯格固然对这些学者意欲欣赏和理解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表示赞同,但他坚持认为,这些思想与自布鲁诺、伽利略、笛卡儿等人开始的时期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一种基本的不连续性,以至于把人文主义者设想为近代的“先驱”并不总是合适的。他建议我们应当把他们的时期解释为反映了“一方面分裂为唯名论,另一方面分裂为人文主义的中世纪的时代危机”。布鲁门伯格在《近代的正当性》的第四部分对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他有时被称为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因此也被说成是“开创了近代思想”)思想的阐述就是这样一个细致而有说服力的解释的例子,这只有在布鲁门伯格的方案中(其中“近代”思想的出现要晚得多)才是可能的。对此,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另一个证明。
人文主义之所以只能是一种不稳定的、过渡性的形成物,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给予其支持者方法以抵御唯名论和一般的奥古斯丁逻辑针对世界和上帝施于其中的神意所提出的颠覆性的怀疑。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许可能会对大学中正统的(阿维洛伊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进行一种“虔敬的”适当指责,后者正是人文主义者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是在神学中,就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布道者的成功所暗示的,上帝中心论、上帝的全能以及人的无助都是中世纪思想让人不得不接受的结论。事实上,包括哥白尼在内的人文主义者都依赖于上帝的善,但只有人的自我肯定(通过停止在一切方面都依赖于他)才能真正解决(符合奥古斯丁逻辑的)上帝的自由致使上帝对于人的善成为问题的方式。
然而,哥白尼避免面对中世纪晚期的这个关键问题,并不意味着唯名论对他的努力没有影响。恰恰相反,它起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作用,不过不是决定了哥白尼主张的内容,而在于使这些主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使得哥白尼能够严肃地考虑它们,也使得他期待其读者也能这么做。这至少因两个理由而成为一个重大的贡献:首先是因为同一种理论在公元前三世纪被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克提出时并没有被认真地对待;其次是因为哥白尼的主张“在数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被提出,这些世纪带着关于世界解释的最封闭的教条体系印记,其基本特征可以被概括为:在他的时代之前不可能出现一个哥白尼。”
所以问题是,那种教条体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哥白尼最终能够成为“可能”?布鲁门伯格的回答有两个部分,分别在第二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得到了阐明。他告诉我们,首先,奥古斯丁的逻辑坚持认为(就像1277年巴黎大谴责中所说的那样)上帝没有必要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方式来安排事物,从而破坏了亚里士多德地心宇宙论和物理学。这一谴责成为思想家的一张通行证,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的假说也许是不可能的,从而不值得考虑。然而,正如哥白尼主义的论争史所清楚表明的,这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再具有权威性,它们仍然是可资利用的唯一广泛的宇宙论和物理学体系,这使得人们很难想象没有它们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它们虽然是唯一广泛的体系,却不再是唯一可资利用的观念。那些设法获得了1277年“通行证”的思想家们的确制造出了一些部分性的替代品,它们的存在是哥白尼被认真对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例如有appetitus partium,即“部分聚合为一个整体的欲望”,作为后来引力概念的替代,它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一个不再“居于中心”的(于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元素寻求其“天然处所”的观念就不再能够适用于它)旋转着的地球不会飞散。还有著名的“冲力”(impetus)概念,作为后来牛顿惯性概念的替代,它有助于说明像下落的石块和飞鸟这样没有与地球接触的物体为什么并不必然像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所推论的那样,被其运动抛在后面(这要求一个推动者通过直接接触而对被移动物体进行连续不断的作用)。
有一种自然倾向把让•布里丹(Jean Buridan)、尼古拉•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和其他发展了这些想法的唯名论者看成本质上在从事“科学”,或者无论如何也是在致力于“自然哲学”,它们实际上与一个希腊的异教徒或一个世俗的近代科学家可能从事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库恩就把经院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形容为“近代世界中第一次有效力的研究”,它展示了“一种对人的理性力量解决自然问题的无限信念”。为了抵制我们自身假设的这种自然投射,帮助我们理解那段很长的时期(大约从1400年到1580年)(在此期间,唯名论者的理论的确已经在意大利大学中教授,但在那里它们并没有导致更进一步的具体发展),意识到这些思想家的实际意图有多么保守是重要的。和所有的经院哲学家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致力于其中的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当他们批评亚里士多德时,他们头脑中所想到的并非是最终需要全新的观念(这也许把他们的注意力导向了诸如做出具体的测量或实验这样的事情),而总是意欲补救继承下来的体系。于是,就像布鲁门伯格所表明的,“哥白尼最明确的唯名论‘先驱’奥雷斯姆[他讨论了地球周日旋转的可能性]背离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恰恰是为了能够拯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通过假定甚至月下天的物体(从而也必然包括地球)也可能作一种天然的圆周运动,从而消除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彗星运动的论述的含混之处。而同样违背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与地之区分的布里丹则沿着相反的方向,通过把冲力概念(它此前曾被用于分析抛射体的运动)应用于天球的运动而不再处于所谓天文学知识的正轨;他只是在把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天然运动作为有目的的运动——的批评进行普遍化,这一批评是由唯名论者强调神的意志不可理解而引发的。正如布鲁门伯格对这一情形所做的综述,“对经院哲学体系思辨可能性的彻底探索旨在展示上帝的统治及其绝对的力量(potentia absoluta),而不是为了拓展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如果它被证明对后者是有效的,那么这是保持体系稳定性的努力的一个结果”。因此,尽管唯名论为哥白尼的伟大步伐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但这一步不可能由一个唯名论者迈出,而只能由某个有理由认为关于天的知识实际上是人可以获得的人迈出——即由一位人文主义者来实现。
关于唯名论有助于“使哥白尼成为可能”的第二个方面,布鲁门伯格在第二部分的第三章(“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型”)中进行了讨论。这一部分的回答与世界的同质性有关,哥白尼认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秩序,因为它是“为我们”而创造的。这里的问题是,在古代,哥白尼后来会依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神意是与把理论理解为本质上是人与宇宙之间的一种视觉关系——“对天的静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布鲁门伯格在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它的历史:参见这篇序言的第6节)。在这样一种关系看来,“静观者”居于宇宙的物理中心(斯多葛派就把他置于此处)是适当的。人文主义既然能够复兴斯多葛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同时又不被卷入斯多葛的地心说,这暗示在那个时候,理论态度已经在原则上变得与其传统上的视觉内涵相分离了——这是一个无法被比如“柏拉图主义”复兴的影响完全解释的结果,因为正如我以前指出过的,柏拉图主义恰恰缺少一种同质的可知的实在的观念。
那么,哥白尼是从哪里获得了对于整个同质世界的认知途径这一观念呢?它既不是斯多葛派所认为的视觉途径,又不是仅仅针对一个理智世界的柏拉图的途径。这是布鲁门伯格在第二部分第三章最后提出的主要问题,他在那里引出了唯名论的上帝与哥白尼世界中的人之间的一种令人惊讶的关系。他指出,哥白尼的目的论前提
不能被理解成一种对(按照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说法)有利于人的部分性的目的论的普遍化;之所以不能这样来理解,是因为它恰恰排除了需要这一要素。它理应确保一条人达到真理的可能途径,这条途径与天文学这门技艺在生活中起作用的方式无关。一种超越于人的需求的满足被刻画了出来——在中世纪,只有在下一个世界中的“神视”(visio beatifica)才能达到这样的满足。布里丹宣称,上帝是一切自然事物的终结,这是在一种统治独立性的意义上说的[即尽管它们“为了他的目的”而存在,但他却并不需要它们],而不是在他不拥有关于世界的任何知识这一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说的。这种关系现在(在创世之后)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纯理论的关系吗?可以被解释为(在那种理论中)世界上一切物体的一种普遍同质性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一转变依其内涵就将延缓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分裂的目的论,并且在客观上将自然的整体特征展示为“参考人”(reference-person),人在哥白尼的方案中再次出场了。
布鲁门伯格的建议是,宇宙首先作为一个“理论”对象通过唯名论的神学被统一起来,从而与《创世记》中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一致。与任何一位希腊神不同,也肯定与阿奎那曾经试图把基督教的神与之进行整合的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不同,这位(奥古斯丁的/唯名论的)神对这个世界感兴趣——因为它是他选择创造的。对他而言,远与近、质料与形式、天与地的区分当然是不重要的。一切事物都无一例外是为他而存在的(被他创造的)。
与其斯多葛派的前人不同,这次重新占领所产生的“为人”的目的论并不暗含任何特别的宇宙论图示,因为它所要求的与实在的关系——“理想化的”中心位置,如布鲁门伯格在下一章中所称的——是在与神的地位的完全非空间的(也是非视觉的)类比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这就是一个与实在之关系的最终模型,它与“柏拉图的”数学主义相容,与斯多葛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容,然而其基本模式却并不依赖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它是哥白尼声言(这激发了他的全部努力)要理解一个同质宇宙的基础。同样是以这种根本的方式,唯名论对于盛期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摧毁是哥白尼变革的一个必要前提,尽管既要采取这种变革又仍要保持为一个唯名论者显然是做不到的。虽然哥白尼并没有像近代的“自我肯定”那样“构建一种能够对抗神学唯意志论的立场”,但他的确通过把人(至少是相对于他的知识类型来说)置于神的位置而不可逆转地超越了这种唯意志论。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六章)中,布鲁门伯格阐述了哥白尼的理论是如何(在物理上和形而上学上)成为“可能的”,并且假设性地探讨了作为一个天文学家的哥白尼是如何达到它的。他通过对《天球运行论》和《要释》(Commentariolus)的详细解读而得出的观点是,哥白尼是从一个只适用于金星和水星的部分性的日心模型出发的,这个构造不是他原创的,而是公元前四世纪庞图斯的赫拉克利德作为解释这两颗行星被观察到永远位于太阳附近的一种方法而提出的。哥白尼接着可能把这个模型推广到也包括其他行星在内,只是作为这一过程的最后一步才把地球插到体系中(从而填补了金星和火星之间的缝隙,使整个图景变得和谐)。地球作为行星,它的周年运动首先被想到,其周日旋转只是一种事后才产生的想法,这样一种可能的思想轨迹的逻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哥白尼的那些“先驱”们(比如奥雷斯姆)考虑了一种可能的周日旋转,却没有走得更远。事实上,他们甚至连哥白尼实际道路的“第一步”都没有迈出。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雅家:六大天王
- 原创男主角女主角
- 4.0万字6个月前
- 梦断南宫
- 生命只有一次,又或许平行世界有无数次。一诺的妈妈会在另个世界依旧陪伴一诺吗?
- 13.4万字6个月前
- 品质少女:情绪精灵
- 自创的魔法少女的故事(◍•ᴗ•◍)
- 2.6万字5个月前
- 旁观者有罪
- 往往查的越多…死的就越快,警告的终端便是死亡,查不到的往往是最危险的,科学的终端是玄学…而玄学的终端则是无尽的幻想……
- 0.6万字5个月前
- 她不是疯子
- 特点:生性自在散漫,不愿受世俗约束,道德感比较模糊,遇好人则菩萨心肠,遇坏人则sha人如麻不是小人,也不愿做道貌岸然的君
- 0.9万字1个月前
- 惋落
- 〈正文已完结〉世上再无林晴,只有司清在三外之境和人界的来回穿梭,司清的心被万落给捂热了。但两人并不是一个空间的人,情爱能长久吗?
- 7.5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