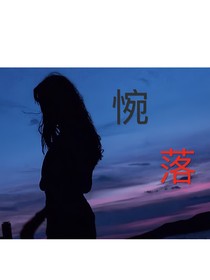哲学(一)
目录
所谓现代 ▹
所谓后现代 ▹
所谓非现代(Non-modern) ▹
原文链接: Afterall - On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on-modern
作者:许煜(Yuk Hui)[1]
再会,幽灵!这世界不再需要你——或我。将一种必将导致毁灭的趋势谓之为进步,世界正为生命寻觅着死亡的裨益。仍会有无解的谜存在;但很快,一切都将变得清晰,最终我们将见证一个动物社会的奇迹,一座完美的终极蚁丘。
——Paul Valéry《精神的危机》
所谓现代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瓦勒里在两封信中悼念着欧洲的精神危机。彼时彼刻现代纪元正处在巅峰,在目睹无数生命以及城市付之一炬后,瓦勒里写道:“1914 年的欧洲可能已经抵达了现代主义的极限。”[2]该现代纪元随后被证明完全是一种浮士德式噩梦。幽灵(Phantoms)——非现代之象征——被驱逐出世界,因为世界正转向彻底的科学性建构与技术性征用。然而,这些幽灵仍旧持续地出没于现代世界中。现代性之特性,乃一种念念有词着无限进步的技术无意识。我这里所谓的无意识,指的是假定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与欲望而推动历史前进,同时又忽视着使诸多意愿具有可能性、使诸欲望变为噩梦的装置。哲学家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在其中瞥见了一种进步派的乐观主义,自相矛盾的是,这种乐观主义正是由技术以及一种想将这些技术设定为透明的念想共同激发而产生的,这恰是西蒙栋于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编纂者群体中所感受到的。[3]此种乐观主义,在十九世纪末,直接见证了属于其自我之悲剧,正如尼采早在几十年前于《快乐的科学》第 124 节中描述的那样,题目是《在无限的地平线上(In the Horizon of the Infinite)》:我们已经抛弃了陆地,去往海洋!我们已经将身后的桥摧毁——不仅如此,我们还毁掉了身后的陆地!现在,小船啊,当心!在你旁边的就是大海;的确,它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咆哮,甚至有时候它静静躺在那里,好似绸缎,好似黄金,好似一串串美好的梦。但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它是无尽的,而世上没有什么比无尽更令人敬畏的了。哦,那可怜的小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现在一头撞在这笼子的壁上!唉,当对陆地的思念淹没了你,就好像那样你会得到更多自由似的——而那里,已经再无“陆地”![4]
相信无限进步的那批人终究会意识到,世上最令人恐惧的其实即为无限本身。那些他们认为可以用于实现人性的技术,最后生成了去人性化之进程,或者导致人类社会沦为一座蚁丘。然而,现代性并未在 1919 年终结。二战尚未降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之灾难的爆发,令对于现代的焦虑始终深深笼罩着欧洲,即便二战已结束七十余年,欧洲依旧未能彻底恢复。与此同时,在东亚,这种焦虑情绪在京都学派的疾声呐喊声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口号“超克现代性(overcoming modernity)”今天时常被与那些爱谈论“总体战”、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之观点联系起来。
尽管我们无法在较短的篇幅内穷尽现代性这一复杂概念,但上述的各色场景已然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现代”这一词携带的不适感;那么这样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的书名了,《我们从未现代过》。[5]然而,现代性始终伴随着我们。几十年来,人们不断努力推翻一种现代性是西方世界专利的假设,我们得以看到诸多概念的发展,一种中国的现代性,一种日本的现代性,一种东亚的现代性等等。2014 年,位于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的展览《多重现代性 1905 - 1970(Modernités plurielles de 1905 à 1970)》展出了近四百位艺术家的超过一千件作品。[6]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尝试,以证明现代性的讨论应该被延伸到欧洲以外。
但现代性究竟是什么意思?除去某种多元文化与平等的矫饰之外,强调从来存在的多重现代性究竟意味着什么?鉴于全球技术加速,思考非现代不是更为迫切了吗?我理解的非现代,并不是那种尚未现代从而将会变现代的东西,而是一些持续抵抗着向现代之转变,并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变现代的东西。
本文旨在证明为何我更倾向于再论非现代,而不是探寻一种民族的或是区域性的现代性,它们可能其实从未存在过且有可能庇匿着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是探讨 Enrique Dussel 的跨现代(transmodern)概念,就像大多数后殖民理论的相关讨论一样,不经意间回避了技术的问题。[7]
非现代如何能成为现代性的避难所?有的人可能会问,通过反对现代与非现代,我们是否依旧是某种意义上现代的牺牲品,这样的抵抗不过为其反动之另一面?为了与非现代一同思考,并超越之,我们必须要阐释明白现代性这一术语。这并非本篇文章的人物,不过我们将简要地尝试说明:首先,现代性必须要和艺术与文学流派中的现代主义作区别——譬如说,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诗歌、波德莱尔的散文还有切塞纳的画;其次,它和现代化之前的区别也必须分清,后者是在欧洲现代性萌芽与发展时期出现的一种认识论普适化之过程,总被人们模棱两可地同现代科学与技术划上等号。非欧洲国家的对“现代性”的追求最终变为了农业、工业、军工以及科学技术上的现代化进程。狭义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间的破裂,始于十六世纪的欧洲。在该层意义上,现代性必然会牵涉到知识之生产,抑或——用康德的话讲——产生知识之可感条件(sensible condition)。就此,我们也许有必要重温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写的:重新思考康德的文字,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将现代性设想为一种态度,而非一种历史时期。此处的“态度(attitude)”,我指的是一种与当下现实产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特定的人自愿做出的选择;到最后,演变为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感受的方式;同样也是一种行动与举止的方式,将自身作为一种任务,标志着一种归属之联结。[8]
对福柯而言,现代性,乃一种特定的思考与感受方式,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知识(episteme),这是他在早期著作《词与物》中的术语,在那本书里他详细辨别了自十六世纪以降的欧洲的三种知识,分别是文艺复兴、古典时代与现代。[9]正因如此,我将此处知识的概念重新阐释为一种产生知识的可感条件。我此处强调感知力的问题,因为正是感知力才使得多种不同知识可以共存。现代化即是一种通过西方殖民手段,通过罗盘与军事技术向欧洲以外的区域传播这种破裂,从而令这些思考与感受方式变得四海皆准的过程。我们或可以说,比如在中国、日本和韩国有这样的一种现代化进程,但我不确定能否理据充分地说这些土地上存在着一种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或是东亚的现代性。我并不是说失去了现代性的现代化一定是坏的,对于理解“坏”这个问题这样的对立并不能起到任何帮助;我只是想说,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以外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同的。欧洲之外,前述的破裂并不是连贯生成的,这种破裂也并不是在与其自身过去碰撞对话中发生的。只能说,只有当历史与传统无法再栖息于持续变化着的技术环境之时,现代化的进程才会加速。
所谓后现代
我认为在分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时候,尤其有必要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件历史事件,而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世界的历史进程,更准确来说,一种全球范围内技术带来的知识普及化。现代性更新了一幅世界图像,一种与哥白尼式转向相反的改变,再次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地理与人类中心主义。这里现代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世界历史表达的支点,从前现代,通过现代,再到后现代。后现代是一种对现代的超克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Enrique Dussel 表明了他的怀疑,并主张对跨现代进行讨论:实际上,“后现代”的一切问题都源于现代性的本质——也就是它依旧是一种“欧洲的”现代性图景——我们于是会发现一直说的“后现代”和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们在 1980 年代暗示的东西是迥异的……因此,我们看到了从“外部”视角重构“现代性”概念之需求,换言之,一种全球的视角(而非如同欧洲视角这种区域性视角)。这很关键,因为“现代性”在美国和欧洲携有(也将继续存在)某种尤其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含义,从利奥塔或是瓦蒂莫(Gianni Vattimo)到哈贝马斯,甚至即便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能让人隐约嗅到那种微妙的令人不适感,对于这种我称之为“二次欧洲中心主义”。[10]
Dussel在这里是对的,溯其源头,所谓后现代是一种对欧洲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如他所说:“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欧美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现代性的『核心』。中国文化或吠陀文化可能永远也无法成为欧洲的那种后现代,相反会因为独特的文化根源,变得形貌各异。”[11]那么,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对于从未真正现代过的非欧洲文化而言,比如中国,如何去拥抱它们的后现代呢?这种不连贯性难道不暗示着一个围绕现代性而构建起某种完美的世界史之想法的彻底失败吗?不过,针对 Dussel 对于利奥塔的批判,我想说跨现代性这个视角忽略了后现代讨论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我称之为技术意识(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
我拒绝——我这样做的理由在别的地方曾经写过——将利奥塔仅仅看作一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家。[12]与现代人之技术无意识相比,自 1979 年以来利奥塔进行的后现代讨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技术意识推动的。技术意识指的是什么?利奥塔 1979 年的著作《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即是对于因技术导致的剧烈社会转变,尤其是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影响之下的转变的一份回应。[13]利奥塔认识到,若要理解这种转变并逐渐改变现代的思考方式,就必须要拥有一种完全崭新的感知力。如果说现代感知力的特点是对于确定性、次序、支配与进步的需求,那么后现代的特点就是各种不安、焦虑、不确定与尊崇的感觉。
换言之,利奥塔发现,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新的技术辩证地又在逐渐动摇着现代性;因此,不能将这些新的技术——从信息技术到纳米技术——视作现代社会的产物或连续,他提出这些技术必须要以一种新的感知力来理解,将这些技术理解为颠覆现代社会的工具。[14]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利奥塔认为的技术是一种需要被夺回(reclaimed)的东西——它拥有一种改变转型的力量从而淘汰掉现代的感知力。虽然利奥塔从未用过福柯的知识型(episteme)来命名自己的后现代感知力,但似乎没有比这更精准的配对了。[15]
无论在西方抑或亚洲,以技术意识作为主题的后现代讨论在这套话语内颇为鲜见。比如对于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而言,后现代即为晚期资本主义之文化逻辑——这种逻辑无非是后现代知识体系的其中一层,但它并不一定真的捕捉到了后现代自身的精神。在几乎所有的与后现代有关的二阶讨论中,技术意识都一直被忽视。在 Dussel 关于跨现代的讨论中也是一样,看不到作为核心角色的技术的影子。不是说 Dussel 没有关注技术,但只是说技术在它的跨现代理论中从未成为某种主题。那么,没有这样一种技术意识,又谈何真正的解放呢?我们来看看 Dussel 的办法:
现代性并不会在通过完成各种行为而传递效力的时候完全实现,而是会通过与它曾否决过的歧途(alterity)发生化学反应。跨现代项目通过现代性实现了无法仅靠自身实现的东西——共同实现了一种团结,通过分析、类比、同步、混合与杂交,从而将中心与外层联结起来,女人和男人,种族与种族,族群与族群,阶级与阶级,人性与地球,还有西方的与第三世界的文化。这种联结并不是在否定中出现,而是通过歧途视角下的一种囊括……[16]
Dussel 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穿透力的对话,可以创造一种囊括并吸收各种不同视角观点后的团结,包括欧洲现代性在内。换句话说,非欧洲文化可以在学习借鉴现代性的同时,从自身视角出发,发展出一套对现代性的批判。然而,在当今全世界都在经受强大的技术力量带来的社会转变的背景下,这样一种穿透性的对话如何可能,我们还尚未得知。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庞大的技术力量是一种西方形而上学的实现。这里所说的实现,指的是在同一时刻终结和完成。于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系统的发展与持续趋同正是一种此类大终结的表现。1964 年,海德格尔写道:“哲学的终结印证了,对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与更适合这世界的社会规范的操控与配置的胜利。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一个建立在西欧思想之上的世界文明的开端。”[17]如果海德格尔是对的,那么世界史之重启唯有在它被视作必需从而超越其并赋予其偶然性之后,才能够完成。[18]我不知道过去几十年来,人们有多少具有穿透性的交流;相反的是,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不断的、各种形式的战争。除非这种庞大的且正改变着地球的技术力量本身成为我们深刻分析与改变的主体对象,否则我们将无法将其颠覆。或者如海德格尔在一篇献给里尔克诗歌的散文《诗人何为?》(Wozu Dichter?)中写道的,“除了来自危险所在之处的其他任何救赎,可能都仍在亵渎神明之处。”[19]
作为给这部分的插曲,汤因比的一条评论在今天看来似乎尤为贴合,那是他尝试解释十九世纪亚洲国家天真烂漫地进口着西方技术时写下的。他说,十六世纪远东的人们拒绝了欧洲人因为后者尝试输出宗教和技术,但到了十九世纪,当欧洲人只输出技术的时候,远东国家的人们便将技术看作一种可以完全靠自己的思维掌握的中性的力量。结果就如汤因比观察到的那样:“这种技术的碎片……最终的确成功推进了远东社会的生活,这个社会曾经拒绝了引入整套西式生活的尝试——技术和一切,包括宗教。”[20]
所谓非现代(Non-modern)
在有关跨现代(transmodern)的讨论进行了几十年后,今天这个词又重新冒了出来,同非现代一道困扰着我们。有什么残存的今天可以重申的新东西吗?又有哪些部分我们可以再更新?我相信Dussel 对于一段完美的历史的批判,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的接替顺序,是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商榷的。将非欧洲国家置于一个基于欧洲话语的世界史框架内是有问题的。但是,仅是脱离出欧洲话语是不够的,因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史」依旧等待着人们开启。对于较流行的线性史观,我想再加一个时间节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大灾变(apocalypse)。这里的大灾变囊括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生态灾难、人类世、机器人反叛、AI 管治、对太空的殖民还有我们正在面对的新冠大流行。根据人类改造增强的承诺,我们最终都将会成为超人(Übermensch),但这依旧是一种对末世论的懦弱渴望,希望灾难发生之后能够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近些年,出于频发的生态灾难和人类已经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论断——人类世指的是一段重申历史人类中心主义的时代——出现了一种提出通过重回非现代来超克现代性的思潮。人类学中所谓的“本体论转向”,与之紧密关联的学者Philippe Descola 和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等,即为一种通过这样拆除现代社会中的类目标签来超克现代性的尝试。这些思想家通过回到非现代来撕去现代的标签。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的接替者 Descola 曾提出要重新检视自然这个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自然被理解为我们身边的非人造的环境。这个概念是一种基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并由现代社会构建而成的产物,Descola谓为“自然主义”。自然于此被视作文化的对立面,同时又是一个供文化去领悟掌握某种「精神」的用品。然而,这种自然主义并不是自然状态,相反它是一个错误。在《超越自然与文化》里,Descola引申了 Henry Michaux 1928 年从厄瓜多尔访友后返归巴黎时的日记。[21]这段旅途需要他们在亚马逊河上独自划一个月独木舟。在与同行者抵达 Belém do Pará 时,Michaux 描述了一个无法用现代的自然概念解释的奇异景象:“我们船上一个从 Manaus 来的女人,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进城了。当来到大公园(无法否认这座公园的植物栽种十分精美)时,她轻轻叹了口气。『啊,终于到了,大自然』,她说,哪怕她刚从雨林出来。”[22]对于亚马逊人而言,像雨林、猎豹或是植物这样的非人类角色的意义与我们今天自然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在这些原住民族群中,基于自然与文化分野的知识形式是无法被简化的。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彩虹的光辉
- 唐彩星成神的故事.这里古月娜他们不是毁灭之神和生命女神,她原本以为自己是唐三的女儿其实自己是生命女神的女儿,因为毁灭之神怕毁灭之力干扰了女儿......
- 2.3万字6个月前
- 失昼之地
- 和平,安定,完美,怀揣善意之人得到幸福,作恶之人被惩戒放逐。这就是吉索达,光明神塞丽蒂亚庇佑的大陆。而正如光影永恒相随,一切事物终有其反面,......
- 1.7万字5个月前
- 清风拂过叶林间
- 四个人一起进入副本,探寻案件。案件一:拼凑娃娃案件二:泥墙母亲案件三:火锅男孩案件四:疯子父亲每一个案件都惊心动魄……“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我......
- 1.8万字5个月前
- 异世界转生重生
- 怎么说呢,男主角转生变成少女
- 1.6万字4个月前
- 惋落
- 〈正文已完结〉世上再无林晴,只有司清在三外之境和人界的来回穿梭,司清的心被万落给捂热了。但两人并不是一个空间的人,情爱能长久吗?
- 7.5万字3个月前
- 爱在世界尽头:我的老公奇形怪状
- 浮世迷津暗涌,痴嗔共咏韶音(会有多个世界,系统会在第二世界出现!)“神明他啊,他亲手创造出了他的爱人......
- 1.8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