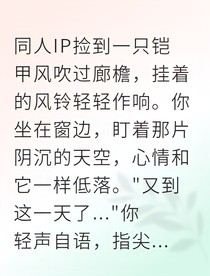法律诠释主义(三)
在涉及法律解释结构上,纯粹诠释主义有一个相关主张。在对法律的正统解释中,制度发布指令,每个指令都传达并由此创造了一个有效的规范。因此,每个制度行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它是在法律中增加了一个有效的规范。这样构成的规范然后被编织在一起,形成法律的完整内容。(这并不是要否认,根据这种观点,一些规范可能恰恰涉及如何将规范编织在一起,例如规定新法优于旧法原则(lex posteriorderogat legi priori))。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是原子化的(Greenberg 2007)。非混合诠释主义则不那么坚定。因为它认为道德决定了制度性实践如何影响权利和义务,所以它继承了道德的整体结构:整个道德面对整个制度性实践,决定了诠释旨在识别的实践效果。制度性实践的特定事件,例如新法律的颁布,通过改变实践的内容来改变权利和义务,进而改变其道德效果(Greenberg,2007,2011a)。
在这种观点上,证成justification)的概念是非常不同的。道德事实固定了其他因素的相关性。反映这些事实的道德原则并没有给法律增加内容,道德原则反而需要与制度所贡献的其他内容相结合。它们决定了制度性实践的哪个确切方面与实践对法律的贡献相关。因此,道德事实是对法律的构成性解释的基础,但并不直接决定其内容。它们决定了制度性实践是如何决定法律的。
这方面的一个熟悉的假设涉及到这样一个原则:在道德相关方面相似的纠纷应该被一视同仁。这个假设要求在案件中确定道德相关的方面,这就强调了涉及挑选出那些方面的进一步假设。考虑一个假想的案例,甲诉乙,乙被命令赔偿甲所遭受的损失,这些损失是乙的行动造成的。在目前的相关意义上,一个原则,例如,一个人要对因他未尽必要注意的过失造成的损害负责,如果这个原则确定了与乙的责任有关的因素,那么它将是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这个原则将在规范意义上解释为什么乙应当被判令赔偿——它将表明这项判令是怎样正确的。同时,考虑到“一视同仁”的责任,该原则将决定这一决定对其他案件有何影响。它将反映出作为适当注意义务基础的事实,以及该原则所阐述的适当注意所带来的责任。在这种假设中出现的原则,首先必须证立解决真实或假设的争议案件的特定方式;其次,证立过去的真实或假设的已解决的案件,即那些通过过去的方式而得到解决的案件之结果,在本案中也没有争议。这种性质的假设具有类似的功能,无论它们涉及制度的行动还是诉讼代理人的行动。通过挑选出制度性实践的某些方面的道德相关特征,关于原则的假设可以解释当今实践中这一方面的法律相关性。
作为备选的其他因素并不局限于制度给出的说法;也不局限于已确定的法律意见所认为的相关因素。也许法院说,乙疏忽造成的损害是使他有责任赔偿的原因。但法院可能没有这么说——它可能提到了别的东西,或者说了一些相冲突的东西。或者它可能提到了疏忽和损害,但可能没有说损害的程度和可能性与预防损害的责任相比,是否与乙未能达到的注意标准有关。法院没有提到这些因素,是否会排除它们与未来案件的相关性?答案将取决于一些进一步的原则,这些原则解释了过去的决定为什么以及如何与当下的案件相关,如果它们相关的话。如果法院应该尊重他们过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或减轻经济交易的其他成本,那么法院未能阐明的原则可能与一案对未来案件的影响无关。但是,如果法院的责任是参与他们过去的决定,因为他们必须整全(with intergrity)行事,那么这种原则就可能是决定性的(Hershovitz 2006b)。
这些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判例法所特有的。一些候选因素可能会合理地决定一项法律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影响。法律文本的字面意思(plain meaning);某些成员或议会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制定文本来表达或声明一些东西的实际(语言)意图(根据某种整体语言意图的观点);他们以某种方式改变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意图,即意图通过使用法律的具体语言来获得某种法律效果;如果他们考虑了一些他们原本没有考虑的情况,他们便会想要达到的其他效果;他们希望法院认为法律具有的效果;他们期望法律被认为具有的效果;他们的二阶意图(intention),即某种一阶意图,例如他们的语言意图,控制着法律的效果;在相关法律颁布之前就存在的政治实践,并且这些实践在当时和之后都不被认为会受到法律颁布的影响(Scalia 1998);法律在其序言或提案中正式宣称的目的;在辩论中为其辩护的理由等等。通常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因此基于这些因素做出的选择不会产生明显的差异。但它们不需要,并且我们总是可以构建假设来检验它们对某些决定对法律的影响的相关贡献。
对于纯粹的诠释主义来说,诠释主义假设就是这样的测试,并且旨在支持相关的理论选择。这些假设诉诸政治道德原则,这些原则证立了制度行动的某些特定方面具有决定权利和义务的作用。通过如此这样做,他们旨在为每个候选的法律决定因素确定其对法律的确切影响,包括当其他一些候选因素导向不同方向时的影响(参见Dworkin 1985、1986、1998;Greenberg, 2004;Stavropoulos 2013)。
候选的相关因素包括以下考虑因素——文本、实践或态度,这些考虑因素涉及候选的因素如何影响法律这一问题。上文提到的关于哪些意图重要的问题(德沃金1985年和1986年讨论过)就是这样的因素,而诠释的准则或惯习和程序性规定则是大家熟悉的进一步例子。这些都不能免于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法律的问题的拷问。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必须有其他因素来决定它们与法律的相关性,即使在理论预设上他们确实具有相关性是合理的。例如,一个诠释性惯习往往会对法庭出于惯习考量来评估的其他制度因素的相关性如何相关的预期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得公平的因素有利于遵守该惯习。如果这样的话,惯习就会被本身以外的因素所支持,而且对任何类似的因素都是如此(关于立法意图,见Dworkin 1985, 1986;关于实践中涉及其他方面相关性的任何方面,见Greenberg 2004)。
在这种观念中,不会出现混合诠释主义的困难。原则的作用是确定制度性实践的法律相关方面。因此在这个观念中,原则一致性包括实践的道德相关方面一致性。如此理解的原则一致性没有为对实践忠诚(fidelity)的事先或剩余的考虑留下空间。纯粹诠释主义者会说,因为我们不是将道德理想和某些由制度性交流内容构成的规范所组成的非道德模式相比较,所以就不会出现我们是否应该用实质(merit)换取一致性,以削弱我们的道德,使其与我们的历史相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把某些理想当作义务的基础,仅仅因为我们的制度没有明确说过任何与之不一致的东西。由于我们问的是制度历史在哪些方面与道德有关,因此正确的答案是由道德事实决定的,而不是由粗略的道德或已经被历史淡化的理想情况所决定。然而,这个答案并没有描述理想的安排——那些我们在不考虑制度历史时应当想拥有的安排——而是描述我们确实拥有的安排的规范性意义。因此,我们不应该担心我们的道德对我们的历史来说过于完美,或者不如那些让我们免于责罚(get away with)的历史,或者担心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考虑道德,就像现在这样,不是为了与历史进行比较,而是为了发现历史造成了什么不同。
5. 为什么制度性实践是重要的
我们一直在讨论制度性实践的哪个方面与法律权利和义务有关。但是,制度性实践的某些或其他方面是如何如此相关的呢?如果在这个抽象的层面上,道德在相关性的解释中不起作用,那么纯粹诠释主义的案例就会被严重削弱。
纯粹诠释主义通过确定一种道德关切(moral concern),这种道德关切给予实践在抽象层面的相关性,并且纯粹诠释主义为制度性实践的规范相关性提供了一个彻底的道德解释。它很典型地从法律实践中一些熟悉的、结构性的特征入手,而且这些特征的存在通常是被默认预设的。第一个特征涉及法律的制度性特征。法律有一个隐含的基本假设,即法律权利或法律义务的主张是以某种适当的方式,根植于过去的制度性决策和政府的常规实践(实际上并不理想的制度安排)中确立起来的主张,并且只有这样确立起来的主张才能得到承认和执行。让我们将这种根据称为一个法律主张的合法性(legality)。第二个特征是这种主张的合法性应该在某些道德问题上发挥作用。法律机构对某人执行的某些主张只有符合合法性条件,并且适当地建立在制度性实践的基础上,才是典型和被允许的。
以下主张并非是不可信的,即采取某种行动的法律义务的存在是为了给不采取行动附加某种制裁,或者每条法律都必须附加一个强制条款。相反,它主张假定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当并且因为它们与政府机构的实践有一定的关系时才能通过政府机构实施。这是一种规范性约束,并不依赖于是否出现了强制执行的情况。这接近于凯尔森的观点,即认为这种合法性本质上是一种界限,将“以团体名义实施的允许的强制”和“并非如此实施的不允许的强制”分开(当然,对于凯尔森来说,这是只需存在于法律视角中的道德界限,不管它是否直接存在;见Kelsen 1952)。
一个熟悉的假设是,现行的道德问题是由机构使用武力或其他强制手段来指导公民行动的有效权力引起的。合法性通过构成如果被允许实施便会对人们提出要求的必要条件,由此被认为是对权力的限制或规范。注意,在合法性的这个特点中,合法性不是道德的过滤器,不是在规范有效性上的道德约束。在相关讨论的假设中,不存在由非道德的检验识别出的的备选规范,在这些规范最终被认定为有效前,要先经过进一步的道德检验。相反,合法性是允许对一个人实施要求的一个条件,是一种适用于任何这类要求的特殊道德检验,包括完全没有根据的要求以及可能通过其他道德检验的要求。(这是1986年Dworkin提出的道德问题和合法性的相应作用,也见于Dworkin 2011。另一种诠释主义假设可能会赋予合法性一个与其他道德问题相关的同样独特的角色。)
根据这一观点,对于法律来说,一个要求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以正确的方式建立在制度历史的基础上,是它可以被允许执行的一个条件。这既是一种(一种关于法律本质的)形而上学的主张,也是一种(关于强制的道德性的)规范性的主张。这一观点告诉我们,制度历史对强制实施具有限制作用的正确解释(即一个对于政治理想的实质规范性解释,这一解释使得历史在道德上与被允许执行的请求相关)是为何决定了关于制度历史如何确定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正确解释(更准确地说,这一构成性解释是对于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以法律上适当的方式建立在制度历史上的解释)。
这个通用的解释性模板可以用多种方式填写。最著名的(Dworkin 1986,2006,2011)主张是这样开始的:对制度历史在权利和义务的确认和执行中的作用的解释是,政府的行动应该在原则上保持一致——这是在道德上一视同仁的美德的某些版本,也许最终可以用一些公平的原因和政府平等对待公民的特殊责任的结合来解释这些美德。
图片
这种方法基于的观点是,撇开紧急情况不谈,如果法律不允许政府行使强制的权力,那么政府行使这种权力就是错误的。在这里,法律是为了约束政府的行动,而它发挥约束的作用被认为是基于政治道德的原因。(回想一下,约束来自道德事实,而不是制度行为的逻辑。)如果政府支持我的请求,强制执行我对你的要求,它必须通过诉诸其制度性实践来证立它的行动。对合法性在行使强制中作用的解释是,政府有一项长期义务,即始终按照诚实的正义观念(honest conception of justice)行事。只有认为它在有关问题上所说过的和所做过的与它现在可能做的有关,它才能开始履行这一义务。正义的性质是平等的。在道德上一视同仁的熟悉要求,将政府在特定场合以它曾经使用过的方式实施强制,或者将在与当前情况相类似的任何其他实际或假设情况下的方式来实施强制。
在这个非混合观念中,实施强制的原则一致性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当局颁布的所有准则或重复过去的错误。其主张是,强制性互动(coercive interaction)的道德使得制度性实践与现在可能或必须做的事情相关。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其他行动(立法、案例等),并以与该行动在原则上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任何过去的行动,如果在为其他行动辩护的方案下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那就是与现在所要做的事情根本无关的行动,应该被当作错误而被搁置一边。我们必须修正我们对过去行动所根据原则的理解,这些原则可能导致我们犯下这些错误。
既然政府必须使其行动在原则上(而不是形式上)保持一致,那么我们应该从这种规范性解释中经过适当阐述得出结论,即某些共同证立制度决定和既定实践的道德原则决定了法律权利和义务。这些是与制度性实践有正确关系的道德权利和义务,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其制度实施强制,而且必须按照要求执行(Dworkin 1986, 2011)。
根据这一观点,强制的道德从根本上解释了实际制度的规范相关性(Stavropoulos 2009)。在政治哲学中,一个相关的令人熟知的假设认为强制性道德在解释社会经济正义的义务中扮演着一个基本角色。根据这一假设,正义的义务(无论是许多哲学家所主张的平等主义,或不是平等主义的)是通过政治关系而存在的,这种关系存在于那些被置于某些政府强制控制下的人之间,并通过设计满足某些约束的制度来实现(Nagel 2005)。在政治哲学中,学者关注的是理想安排,强制是否如此重要,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这个问题在法律方面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而在法律方面我们关注的是实际安排的规范效果。
如上所述,非混合诠释主义并没有诉诸与实施强制相关的平等主义问题。证明制度性实践在产生义务中所发挥的假定作用的替代解释可以建立在公平预警的基础上(参考Dworkin 1986年所称的“惯例主义”学说)或其他政治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可能包括与权威有关的因素。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边界的。对于正统观点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正统观点主张通过制度来源来施加义务,但对于纯粹诠释主义来说,这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在纯粹诠释主义看来,没有任何义务是仅通过制度的偶发行动来解释的。
回顾在目前的进路中,一些道德上的关切使制度性实践与权利义务有关,并使得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真正的道德权威。但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任何行动,只要有道德后果,甚至改变权利和义务的行动,以及任何权利和义务的改变,都应被视为属于法律范畴。诠释主义者认为制度性实践和法律权利义务之间的正当联系必须是对法律实践所特有的道德关切的适当回应。根据我们所讨论的假设,强制实施引起了人们的关切。因此,如果一项权利或义务要被允许执行,法律的观念就必须阐明这种权利或义务与制度性实践之间的关系。(回想一下在这个假设下,道德关系是合法性的关系,而且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合法的,是因为它们与制度性实践有关)。如此理解的合法性要求似乎对可能构成法律权利和义务基础的制度性行动或制度性实践的其他方面施加了程序性和其他性质的限制。官员们经常公开宣布他们的未来举措,以塑造他们的目标受众的期望,从而影响受众的行动(就像欧洲央行行长在英国政府组织的一次重大投资会议上宣布,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欧元,Draghi 2012)。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做出旨在提高期望值的保证时,我们就会因此改变我们对那些被保证人的责任,这些责任通常是我们有义务去履行的。但是,没有理由期望官员在正常程序之外会采取的这类行动,其本身就会影响任何法律权利或义务。同样,也没有理由排除它在确定其他程序上适当的机构行动或做法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上发挥一些作用。
出于类似的实质性原因,以下观点并不能从其将法律权利和义务视为制度性行动的道德后果的观念中得出,即诠释主义不能区分这些在制度性行动中获得的可执行的权利和义务,而制度性行动作为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塑造者,在适当的观念上,它一方面是为合法性的价值服务,另一方面是这些权利义务下游的进一步道德后果。根据讨论中的假设,如果权利或义务与制度性实践之间的确定关系能实现实践中的原则性一致,那么它就能减轻相关的道德关切。(更详细的讨论在这一节和第四节)。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区分Albert的法律义务,他在一些新的医保法律颁布后,相应地为他的员工购买了新的、更贵的医保项目,并且他还对他的家庭承担进一步的衍生责任,即在他的业务支出增加的情况下,要减少其个人指出来维持收支平衡。在这个假设中,Albert有法律义务购买新的、更贵的医保项目,因为一旦新的立法被纳入制度性实践,这就是实践中的原则一致性所要求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说义务的存在是由于立法对法律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改变对Albert的财务产生了影响,加上某些似乎与立法主题和立法原则无关的个人情况和常规(standing)义务,Albert开始有了一些财务审慎的义务。根据这些事实,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义务与制度性实践有正确的关系,因为立法已经改变了这一关系,并将其划为真正的法律义务,这些法律义务的承认和执行将有助于原则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义务的改变是由于立法对法律做出的改变——不过,立法对Albert的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仍有可能影响到他可能拥有的先前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的某些方面,例如抚养子女的义务。
6. 争议
将强制执行权利和义务与制度性实践联系起来的基本假设,通过设定诠释难题来确定讨论的主题。然而,请注意,它并没有上升到通常所理解的概念性约束。因为该理论把它当作关于制度性实践的规范相关性的普遍持有的道德假设。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假设,它不能免于怀疑,而是要接受批判性的审查。只要另一种假设能够使其他共同的理论前提(pre-theoretical commitments)可被理解,就仍然有可能一以贯之地拒绝将其视为错误的假设。德沃金(1986)称之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学说说明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拒绝将可允许的强制依赖于如上所述的“合法性”,而是建议在前瞻性因素证明这样做是合理的情况下执行义务的要求。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主张与制度性实践的关系只是为了战略目的而被援引。我们可以说,将实施强制与制度性实践联系起来的假设固定了而非决定了法律理论的主题。此外,基本假设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它所设定的诠释问题的回答。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建构性解释的难题:制度性实践如何在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构成性决定中发挥作用。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戏子中的女孩:等着,我不会忘你
- 主角世界观十分宏大,至今为止,网上绝对没有一个人能超越!更改中……更改内容,名字题目这只是第三本的一个介绍,介绍世界世界观的一本小说,我只能......
- 2.9万字8个月前
- 末世语阳
- 女主角酚易:一个坚强、聪明、有领导力的女性,末世前是医生。男主角白莱:一个勇敢、机智、有责任感的男性,末世前是军人。在共同的战斗和生存中,酚......
- 2.0万字8个月前
- 奇思妙想,各种各类小说合集
- 此文不只有一个故事,很多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短篇小说。第一篇:花心痞帅硬汉;季北辰VS独立理智坚韧冷艳美女;莫希。(现代言情,花心浪子遇真爱......
- 4.2万字4个月前
- 梦境荒原
- (真·佛更,可能会删稿大改)你的确是正确的,你曾让我的生活如此梦幻。然而,当美好的事物都在悄然流逝,无论是在黑夜,还是在白天,无论是有声,还......
- 1.2万字4个月前
- 铠勇少女与五灵兽的守护之约
- 同人IP捡到一只铠甲风吹过廊檐,挂着的风铃轻轻作响。你坐在窗边,盯着那片阴沉的天空,心情和它一样低落。
- 3.3万字1个月前
- 恶意审判
- 一对兄妹的故事
- 1.9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