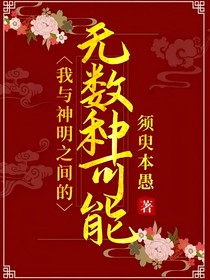哲学(三)
考虑到大陆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中数字和方法的重叠的这些例子,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区别方法。人们可能会说,女权主义更多地关注性别(从历史上,在大陆女权主义中,这可能会以性别差异的形式更常见),而酷儿理论则更多地关注性(包括愉悦,欲望和色情问题)。然而,许多人在大陆女权主义中工作,尤其是在法国理论中受到影响,也集中在与诸如愉悦,欲望和色情主义等性有关的问题上。而且,也有理由怀疑如何将性别 - 性分裂叙述为女权主义者划分。尽管有些人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在这些领域之间进行区分,以便对他们独特的关注伸张正义(G. Rubin 2011; Halley 2006),但对于此分离的过度编程形式也存在许多挑战(Huffer 2013 )以及说明这种叙述如何忽视该领域在理解性别与性别之间复杂关系以及酷儿女权主义的可能性方面的共同兴趣(Jagose 2009)。然而,尽管人物和档案中有重叠,以及大陆女权主义哲学家拥有亲爱的酷儿理论中的丰富资源明确标记为酷儿理论的文字已经显着(Winnubst 2010)。这并不是要删除在这些领域的交集中所做的重要工作,而是要承认这种关系不是无缝的。 Lynne Huffer和Shannon Winnubst(2017)在对“大陆女权主义的圆桌会议”的介绍性评论中指出,在贡献中相对缺乏与酷儿理论的参与,他们询问大陆女权主义是否足够宽敞这也更广泛地构成了哲学(Ahmed 2016b; Salamon 2009; Winnubst 2010)。
最后,大陆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也因其档案的白人和盎格鲁性质而广泛批评。凯茜·科恩(Cathy Cohen)在对这种批评的一种特别众所周知的演绎中,询问酷儿理论是否已经符合其在跨差异中建立联盟的反身份承诺(2005年)。作为干预酷儿理论的白度的一种方式(Johnson and Henderson,2005年),Roderick Ferguson(2004)创造了“色彩批评的酷儿”一词,以描述种族,性别,性别和阶级的各种交往在民族主义的戏剧中运作身份和归属;用弗格森的话来说,这是
由女权主义女性,唯物主义分析,后结构主义理论和酷儿批评组成的异质企业。 (Ferguson 2004:149)
该子场地的其他著名和早期贡献者包括JoséMuñoz,E。PatrickJohnson,Chandan Reddy和Gayatri Gopinath。尽管关于身份,体现,时间和情感的酷儿批评的主题也是大陆女权主义者的核心利益的主题,但与酷儿理论一样,对颜色批判的酷儿的吸收在大陆女权主义方面一直很慢。但是,正如大陆女权主义的扩展(如通过本条目所示),酷儿理论的资源和颜色批判的酷儿的资源在翅膀上等待着至关重要的,如果有时被公认的,对话者。
像大陆女权主义一样,酷儿理论和色彩批评的酷儿仍然是女性主义的长期以来,即以方向发送文本和思想的长期以来,他们也许从未打算旅行过。大陆女权主义和酷儿研究十字路口的最新轨迹包括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关注(Winnubst 2015; McWhorter 2012),古希腊形而上学中的性别和性别(Bianchi 2014);批判性残疾理论(PUAR 2017; K. Hall 2014; Yergeau 2018; and Gallop 2019),拉丁女权主义和存在现象学(Ortega 2016),情感与时间性(Ahmed 2019; Amin 2017; Amin 2017; Freeman 2017; Freeman 2019)以及代理机构的唯物主义和概念(Chen 2012)。正如下一节所探讨的那样,大陆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对话者是变性研究。
5。大陆女权主义和跨性别研究
许多学者指出了跨性别,女权主义者和酷儿框架之间共享和明显关注的复杂相互作用(Namaste 1996和2009; Prosser 1998; Heyes 2003; Heyes 2003; Salamon 2010a; Stryker 2004)。跨性别研究在1990年代成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探究领域,分享了许多酷儿理论的知识渊源,同时也通过其明确的专注于跨性别经验而偏离了酷儿研究,包括这种经验的非单石器性质及其重要性跨性别者为自己谈论自己的生活。同样,虽然大陆女权主义核心的许多理论框架和数字都存在于反式研究(例如,后结构主义,现象学,福柯族家谱,唯物主义)中,但对大陆女性主义方法如何忽略或如何忽略或批评边线跨性别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中引用的大陆女权主义和跨学科的跨学科界限中引用的许多哲学家。
在探索大陆女权主义者与跨性别研究之间的关系时,至关重要的是要承认跨性别恐惧症和跨性别态度可以在女权主义话语中假设的形式。有关此历史的扩展概述,请参阅《女权主义观点》上有关跨性别问题的条目。该条目解释了术语(跨性别,跨性别,变性)的术语,以及跨性别研究的历史出现以及女权主义者与跨性别者之间的更广泛的(即,非洲特定的)关系。
在一种广泛认可的女权主义跨性别恐惧症的形式(在诸如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等跨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工作中发现),跨性别妇女被描绘成不是“真实的”女性,并且是对女权运动的威胁(Bettcher 2006,2006; McKinnon 2018) 。但是,还有一系列女权主义理论与跨性别问题有着独特的关系,并且(重要的是出于目前的目的)它是女权主义的血统,在大陆人物(例如巴特勒)上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女权主义。毫无疑问,巴特勒的作品是跨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的基础(Gerdes 2014; Salah 2007),但她的工作也受到了选择性使用跨性别经验的批评(Prosser 1998; Namaste 1996;批评者指出,跨性别的女权主义话语可以肯定跨性别的身份,当时可以用来证明性别的实际结构,或者其缺乏本体论的必要性,但同样,当某些跨性别身份被描绘成有问题的本质主义者时,伴随着声称是有问题的本质主义者。 “真的是”男人或女人和/或对医疗过渡的要求(Valentine 2012)。尽管普罗瑟(Prosser)和鲁宾(Rubin)都从现象学的角度批评了对性别现实性的拒绝(也从精神分析框架中)批评,但Namaste(1996)着重于这些辩论中经常偏向于性别的制度现实。作为回应,杰克·哈尔伯斯塔姆(Jack Halberstam)认为,尽管普罗瑟(Prosser)在Queer和女权主义理论中选择性地使用跨性别身份的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性别真实思想固有的规范性仍然存在重大问题(2005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致力于跨性别问题的非经历的女权主义作家的扩散导致雅各布·黑尔(Jacob Hale)的“建议的非穿透性人士有关撰写有关变性人,变性,变性,变性主义或跨性别的规则”(1997年[1997 [其他Internet Resources])。在黑尔(Hale)和跨性别研究的出现之后,重要的非反应女权主义分析包括Cressida Heyes(2003)和Naomi Scheman(1996,2016)的工作,他们均表达了CIS和Trans Feminists之间团结的理论基础。 CIS女权理论家将跨性别问题直接带入自己的工作中,而不是作为思想实验(Ahmed 2016b; Colebrook 2015; Shotwell&Sangrey 2008)并与Trans理论家合作(Heyes&Latham 2018)。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顺式”一词本身也受到了更多的学术关注(Aultman 2014)。尽管该术语的最初意图是使非经常性主题的立场变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该一词成功地破坏了性别规范,尤其是在这种规范是种族化的情况下(Enke 2012b)。
最近,在大陆和跨性别方法的十字路口建立了许多新的轨迹。许多哲学家在现象学和跨性别研究的交集中写了许多哲学家,尤其是在批判现象学中,这强调了压迫和权力的问题,以研究世界上的事物如何出现在世界上(Weiss,Murphy和Salamon 2020)。以法莲·达斯·詹森(Ephraim Das Janssen)使用现象学,包括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作品,以研究变性者经验告诉我们有关性别的信息(2017年)。梅根·伯克(Megan Burke,2019年)采用博维尔人的概念来探索雄激素,跨性别身份和出色的经验。盖尔·萨拉蒙(Gayle Salamon)借鉴了莫里斯·梅洛(Maurice Merleau-Ponty)的工作,以在拉蒂沙·金(Latisha King)的生与死中发展出跨性别的现象学(2018a)。 Salamon将现象学和跨性别研究(H. Rubin 1998; Prosser 1998)与批判现象学合并了早期工作的传统。 Tamsin Kimoto(2018)还使用Merleau-Ponty和Frantz Fanon来探索激素过渡和跨性别恐惧症。
沿着类似的线条,精神分析和跨性别研究的新工作也正在修改长期以来的性和性别的心理分析方法,包括强制性和病理学理论跨性别的理论(Elliot 2014),并正在使用精神分析中的资源来从较少的病理学角度来理论化跨性别的经验(Breslow 2017; Carlson 2010; Coffman 2017; Cavanagh 2010)。例如,艾米·雷·斯图尔特(Amy Ray Stewart)使用朱莉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亲密起义”概念来阐明《心理生活》(2017年)的跨性别和酷儿体验。帕特里夏·格罗维奇(Patricia Gherovici,2017)撰写了有关跨性别现象的文章,以及使用拉卡尼亚理论和她自己与跨性别者合作的临床经验来修改心理分析概念的必要性。 Salamon(2010a)依靠精神分析和现象学框架,也捍卫了巴特勒对性别的叙述,反对上述对跨性别经验的批评,并发展了自己的心理分析和现象学对性别和外部外观之间的不和谐的说明适合跨性别体验的身体。
还有一系列的工作,将基础数字置于大陆女权主义与跨性别研究的对话中。玛丽·德拉兹(Marie Draz,2018年)将尼采的女权主义哲学用途置于诸如巴特勒(Butler)(1990)和罗莎琳·迪普罗斯(Rosalyn Diprose(2002)的工作中尽管性别和性别学者已经利用Irigarayan资源来讨论跨性别和酷儿问题,但Irigaray自己的主张是本体论是性别性的,并且性别之间的限制是无法避免的,或者传达了无法抗拒的交叉性的,或者是对非交易经验的特权。同样,奥利·斯蒂芬诺(Oli Stephano,2019)批评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强调性别差异的不可约性,这表明她的本体论无效反式体现和主观性。对格罗斯的这种批评介绍了伊娃·海沃德(Eva Hayward,2017)对格罗斯一些女权主义唯物主义论点的跨性别含义的早期作品。盖尔·萨拉蒙(Gayle Salamon)还批判性地研究了性别差异是对Irigaray和Grosz作品中实施和物质性重新想象的限制的方式(Salamon 2010a)。玛丽亚·卢格尼斯(MaríaLugones)是大陆女权主义中普遍使用的另一个人物,他经常在跨性别问题的奖学金中引用(Bettcher 2014b; Dipietro 2019; Draz 2017a; Draz 2017a; Malatino 2019)。最后,像巴特勒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跨性别研究中使用福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福柯(Foucault)在现代权力类型上的工作已被使用(与有色女权主义的妇女,土著奖学金和许多其他来源一起使用),以研究国家机构如何在性别性有性机构中管理法律性别类别造成的暴力行为( Spade 2011 [2015])。福柯女权主义者对监狱和惩罚的记载也已与植根于跨性别和性别不合格的经验的奖学金进行了交谈(Dilts 2017; Vitulli 2018; Zurn 2018; Zurn 2016,2016,2019)。
跨性别研究继续以不同的静脉发展,这是大陆女权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通过将大陆哲学的工具带入性,性别和性别问题,反之亦然,反之亦然,它不断地将这些对话置于新的方向上。这项工作的大部分是由批判理论的其他领域(例如批判种族理论和非殖民理论)所告知的,并推动了大陆女权主义的传统界限。例如,有关黑人和跨性别历史的最新奖学金已经阐明了发展框架的重要性,能够从历史上和今天(Snorton 2017)了解种族化性别的维度,并从事移民和拉丁裔跨性别者的工作,强调了两者都需要参加这两者。我们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有色人种的生产能力产生新世界(Pitts 2018)。当前关于大陆女权主义与跨性别研究之间关系的对话也必须涉及对学院本身的物质条件的关注,因为越来越广泛地关注哲学上的跨性别经验并没有导致更多的跨性别声音和跨性别学者(Bettcher 2018(其他(其他)互联网资源);大陆女权主义和跨性别研究的未来方向将不仅要注意这些对话中发生的有趣的哲学问题,而且还需要对允许跨性别奖学金蓬勃发展的特定轮廓进行。
6。大陆女权主义和亚裔美国女权主义思想
本节探讨了大陆女权主义与亚裔美国女权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带来了大陆女权主义的新方向。这两个领域之间融合的主要点是关注亚裔美国妇女的生活经验。本节首先讨论亚裔美国妇女由于面临的特定压迫形式而导致的过度掩饰,即东方化和模型少数族裔神话。然后,它突出了亚裔美国女权主义现象学家在工作体内的矛盾形式。接下来,本节考虑了亚裔妇女在联盟女权主义项目中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专注于亚裔美国人妇女被降级为“标签”群体的方式。最后,本节将重点介绍与亚裔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相关的大陆女权主义的最新奖学金,并借鉴了东方和西方的传统。
必须从一开始就指出,“亚洲人”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术语,被认为是亚裔美国人的人民在整个历史上经常发生变化。根据亚裔美国人妇女的选集,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本节介绍了将其根源追溯到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的妇女的身份(加利福尼亚亚洲妇女联队,1989年;南方妇女;亚洲血统集体1993)。
在这座桥上称为我的背(Moraga&Anzaldúa1981 [2015]),亚裔美国人思想家,例如Genny Lim,Merle Woo,Nellie Wong和Mitsuye Yamada,在女权主义中建立了自己的立场,通过探索自己的观点,以探索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性格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身份,杂物为单位的看法。性,沉默,不屈服的感觉以及对亚裔美国妇女的刻板印象,温顺,安静,愉快和顺从。同样,在这座桥上,我们称之为家(Anzaldúa&Keating,2002年),Minh-Ha T. Pham,Shirley Geok-Lin Lim和Jid Lee从她们作为亚裔美国人移民妇女所面临的特定经历中理论理论,例如探索联系对于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亚洲母亲来说,他们仍然持有他们仍然与他们可能从未访问过的土地的文化联系,并在少数族裔神话的面前生活,同时也颠覆了刻板印象。以亚裔美国人和亚裔亚裔女性的观点为中心的著作对于亚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索尼亚·沙阿(Sonia Shah)强调,
[a]亚裔美国女权运动是唯一代表亚裔美国妇女利益的运动。 (1998:XIX)
两次早期选集对于亚裔美国女性主义的形成非常重要:浪潮(加利福尼亚的亚洲妇女联合[AWUC] 1989)和禁忌针迹(Lim&Tsutakawa 1989);它们都包括来自不同种族和国家背景的著作,尤其是中国,日本,菲律宾,韩国,越南人和印度人(Hill-Collins&Bilge 2016:73)。在最近的题为《亚裔美国女权主义和色彩政治女性》的著作中,编辑林恩·富吉瓦拉(Lynn Fujiwara)和谢里恩·罗沙拉万(Shireen Roshanravan女权主义妇女奖学金的中心(Fujiwara&Roshanravan 2018)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与神明之间的无数种可能
- 【双向暗恋+一见钟情】都说神明普度天下,潞鸢却不赞同。初入九重天,潞鸢带着灭族之痛,一腔怒火,此生只为手刃仇人与神明。再入九重天,他带着身后......
- 10.8万字3个月前
- 无声陪伴
- 十七年的陪伴最后却无能为力
- 0.1万字3个月前
- 景西苑
- 不喜勿喷,四男主,修仙+重生司景与顾悬等人携手修仙,在终于成神之际,两人双双陨落,却受到了魔界的影响,重回人世间。这时,洛衍西出现了,在司景......
- 1.0万字3个月前
- 777号玻璃树:属于我们的世界幻想
- 有关于维持世界时空的失落之石遭到破坏爆炸导致世界重组后,发生在一个先进的信息文明,以玻璃树作为主角视角的探索故事
- 0.5万字3个月前
- 幻境大陆
- 一本属于和魔法相似的魔法小说,一共有十位主角,五位男生,五位女生。不要把其他人当配角看,重复一遍“十位主角”。
- 3.2万字2个月前
- 怪异的小妹
- 林家有三子,两男一女。大哥名林萧,二哥为林子洲,三妹唤作林墨。那林墨满月之时,宴席上邀请了各大世家共同庆祝,却突发异状,她小脸泛红,哭声不止......
- 2.3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