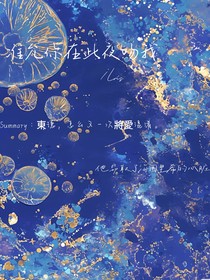列奥·施特劳斯(一)
1. 生活与工作
2. 争议
3. 深奥主义
4. 现代性的神学政治困境
5. 哲学与启示
6. 重新审视神秘主义
7. 古今之争
8. 重温哲学与启示
9. 施特劳斯对启示录的道德论证
10. 重新审视争议
11.施特劳斯哲学的遗留问题
参考书目
施特劳斯的作品
二级文献
学术工具
其他互联网资源
相关条目
1. 生活与工作
施特劳斯于 1899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德国的一个乡村小镇基希海因 (Kirchhain)。他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并在附近马尔堡的一所中学学习,在那里接受了广泛的人文教育。十七岁时,施特劳斯成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比利时担任了一年的军队翻译,之后开始在马尔堡大学学习,新康德主义犹太哲学家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1842-1918 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康德主义学派。 1921 年,施特劳斯在科恩的学生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 年)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论文“F.H. 雅可比哲学学说中的知识问题”。施特劳斯的论文考虑了雅可比的启示概念对知识问题的影响。尽管施特劳斯认为他的论文是“一场可耻的表演”,但神圣启示的意义和地位问题将继续困扰他一生。
1922 年,施特劳斯在弗莱堡度过,在那里他参加了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讲座。施特劳斯很快就被胡塞尔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所吸引,他后来写道: ,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其他当代思想家所没有的。次年,施特劳斯开始在法兰克福成人教育中心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 年)创立的自由犹太教育中心 (Freies Jüdische Lehrhaus) 的赞助下讲学。 1925 年,朱利叶斯·古特曼(Julius Guttmann,1880-1950 年)邀请施特劳斯前往柏林,为犹太教科学院编辑摩西·门德尔松作品的周年纪念版。 1930年,施特劳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献给罗森茨威格的纪念,书中他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斯宾诺莎的读者之所以能把他视为“沉醉于上帝的人”,只是因为他们不再接受上帝的教诲。神圣启示的可能性严重。
1932年,施特劳斯对卡尔·施密特最近出版的《政治的概念》一书进行了评论,他在书中指出,尽管施密特试图采取其他做法,但施密特仍然处于现代自由主义的视野之内,因为他无法为他的观点提供理由。对他所谓的“政治”的规范承诺。施特劳斯后来的许多批评者都将他关于施密特仍然是自由主义者的说法解读为他们认为施特劳斯反自由主义愤怒的证据。然而,施特劳斯对施密特的批评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为施特劳斯终生担心的证据,即现代自由主义面对道德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施特劳斯所谓的“市侩主义”,是否有能力证明其对自由理想的规范性承诺是正确的。其中说“实际上,人们不必思考为什么那些[自由主义]的东西是好的”(WPP,21)。如果现代自由国家对价值问题不偏不倚,那么自由国家如何证明其自身价值的合理性呢?施密特声称没有人像施特劳斯那样理解他,施特劳斯后来声称阅读施密特改变了他自己对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问题的取向。
1932年,由于犹太教科学院的财政问题,施特劳斯发现自己失业了。凭借施密特的推荐信,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开始在法国研究霍布斯。在巴黎,施特劳斯参加了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和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主持的黑格尔研讨会。第二年,他获得了洛克菲勒资助的延期,可以在伦敦和剑桥撰写有关霍布斯的书。
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研究恰逢希特勒上台。施特劳斯因此将注意力转向了霍布斯,他认为霍布斯是自由国家的奠基理论家,而此时德国自由国家的理念似乎正在崩溃。施特劳斯的第三本书《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基础和起源》于 1936 年出版。该书将他新发现的对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关注与他之前关于斯宾诺莎对宗教的批判的著作联系起来,该书关注的是施特劳斯声称现代自由主义与其对宗教的批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935 年,施特劳斯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哲学与法律:对理解迈蒙尼德及其前辈的贡献》。在这里,他所生活的政治现实也与他的学术追求重叠。在格肖姆·肖勒姆的敦促下,施特劳斯将三篇关于迈蒙尼德的独立论文写成了一本书。肖勒姆和施特劳斯希望《哲学与法律》的出版能够帮助施特劳斯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中世纪犹太哲学的职位。施特劳斯没有获得这个职位,这个职位被授予了朱利叶斯·古特曼(Julius Guttmann),他是施特劳斯在犹太教科学院的导师,也是哲学和法学批评的主要目标。
《哲学与法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古特曼假设的攻击,即中世纪犹太哲学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认识论。古特曼认为,研究中世纪犹太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中世纪犹太哲学家,尤其是迈蒙尼德,如何理解作为知识来源的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关系。相反,施特劳斯认为,迈蒙尼德的基本关注点不是认识论,而是政治。在提出任何有关知识基础的问题之前,必须回答在法律权威的框架内进行哲学思考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可以阐明法律的含义,但哲学不能导出法律本身。相反,法律是哲学的前哲学背景和框架。也是在哲学和法律的背景下,施特劳斯开始考虑他之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回归前现代哲学。
1937年,施特劳斯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访问讲师职位。次年,施特劳斯成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客座研究员,该学院是许多欧洲移民的家园。施特劳斯在新学院的职位成为永久性的,他在那里呆了十年。
施特劳斯在新学院度过的十年可以说是他的学术生涯中最富有成果的,当然也是最关键的。在新学院的第一年,施特劳斯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成为 1952 年出版的《迫害与写作艺术》一书。在这些文章中,施特劳斯认为,在阅读某些前现代思想家时,有必要阅读字里行间。迫害的可能性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写作,这种写作允许一组读者(大多数)接收一个信息,同时允许第二组读者(哲学精英)带走另一组信息。虽然这种类型的写作通常被称为“深奥的”,但更正确的理解是“外显的”,即表面上掩盖某种秘密教义的写作。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迈蒙尼德、犹大·哈勒维和斯宾诺莎都是通俗作家。尽管迈蒙尼德和斯宾诺莎之间存在深刻的差异,但他们表面上都教导说哲学和启示是可以调和的。然而,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论点实际上表明了相反的观点:哲学和启示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另一方面,哈莱维表面上教导说哲学和启示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哈莱维在面对启示时对哲学的否定似乎表明哲学不是对启示的挑战,施特劳斯认为,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哈莱维的论点实际上表明了相反的观点:哲学不仅是对启示的挑战,而且是对启示的挑战。极其危险的一种。
在新学派时期,施特劳斯还更深入地研究古代哲学,探索迫害和写作的主题。施特劳斯的第四本书《论暴政:对色诺芬《希罗》的解读》于 1948 年出版。尽管柏拉图《理想国》的主流解读认为柏拉图主张哲学家应该统治,但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实际上认为这种情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需要非哲学家、不明智的人的同意。 《论暴政》关注施特劳斯所说的智者统治的必要条件,即只有智者才能确保城市的正义(OT,193)。在这项研究中,施特劳斯仔细阅读了色诺芬对话的修辞,对施特劳斯来说,这强调了对真理的哲学追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施特劳斯于 1949 年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职位,并在那里任教直至 1967 年退休。加入芝加哥大学后,施特劳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讲座,该讲座将于 1953 年在同一大学下出版。标题。 《自然权利与历史》仍然是施特劳斯最著名的美国著作,但其基本担忧是他早期对二十世纪哲学应对政治和道德相对主义挑战的能力的怀疑的延伸。在美国,在芝加哥政治学系,施特劳斯批评了他所认为的社会科学所依赖的道德相对主义。他在本书的开头分析了社会科学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并试图展示从韦伯的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直接路线,施特劳斯将历史主义定义为“所有人类思想或历史主义”的观点。信仰是历史性的”(NRH,第 25 页)。然后,他将霍布斯开始的现代自然权利概念与柏拉图开始的古代概念进行了对比。施特劳斯认为,前者最终导致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其中不存在超越特定历史背景的道德、政治或科学标准。 《自然权利与历史》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回到某种自然概念来理解我们作为人类的身份,从而回到某种绝对道德标准的概念,尽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施特劳斯晚年还出版了另外两本书和许多论文。 1958年,他发表了可能是他最具争议性的研究《马基雅维利思想》,其中他宣称马基雅维利的“反神学愤怒”是现代性的根源。从芝加哥退休后,施特劳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男子学院任教一年,然后与他的老朋友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1899-1978)一起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担任住宿学者。施特劳斯于 1973 年去世。《柏拉图法则》的论证与作用于 1975 年出版。施特劳斯去世时,还一直在研究尼采、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此后,施特劳斯的一些重要论文集由他以前的一些学生编辑和出版。
2. 争议
围绕施特劳斯和他的作品存在许多争议。首先,近年来,施特劳斯被指责为新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思想教父,从而成为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计划背后的思想力量。其次,施特劳斯作品中没有哪一个方面像他关于神秘主义的主张那样受到激烈争议。对施特劳斯的神秘主义观点的解释包括:施特劳斯主张秘密阴谋,将秘密从老师传授给弟子;施特劳斯的著作本身就是深奥的文献;施特劳斯认为所有思想家的写作都是深奥的;施特劳斯声称知道一个秘密;施特劳斯宣扬大规模欺骗和永久战争;在一种特别粗略的描述中,施特劳斯用他深奥的方法来隐藏他对法西斯的同情,即使不是他秘密的纳粹主义。在探索了施特劳斯作品的广泛主题和背景之后,本文将重新考虑有关施特劳斯的这些不同的主张。
3. 深奥主义
施特劳斯关于神秘主义的主张应该在他一生工作的更广泛轨迹中被理解。这种方法实际上符合施特劳斯自己关于如何阅读深奥或其他哲学文本的建议。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对给定文本的解释必须“从对作者明确陈述的精确考虑开始”。然而,“在对陈述的解释可以合理地声称是充分的甚至是正确的之前,必须完全理解陈述发生的上下文”(PAW,第 130 页)。转向施特劳斯关于神秘主义主张的背景,有助于阐明他作品中的许多其他重要主题,包括他所说的“现代性的神学政治困境”、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论,以及启示之间的关系。和哲学(施特劳斯也称之为“耶路撒冷和雅典”)。
在施特劳斯首次发表关于迈蒙尼德是一位深奥作家的论点时,他自觉地审视了撰写深奥文本意味着什么。施特劳斯清楚地指的是他自己,他写道:
任何一个有正派意识并因此对迈蒙尼德这样的高人有尊重感的历史学家都不会轻松地忽视迈蒙尼德强烈要求不要解释《指南》的秘密教义。可以公平地说,一个解释者在试图解释秘密教义时,也许在第一次感知到它的存在和意义时,如果没有感到良心的痛苦,就缺乏对主题的亲近感,而这种亲近感对于真正理解任何书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对《指南》的充分解释问题主要是一个道德问题。 (PAW,第 55 页)
施特劳斯认为,在试图回答仅在文本中暗示的秘密教义是否可以被自信而准确地理解的问题之前,有必要考虑其道德含义以及愿意写作的作家的道德动力。关于这样一个秘密。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施特劳斯将自己的困境与迈蒙尼德的困境联系起来,通过这样做,他指出了指导他自己关于神秘主义的主张的基本动机。因此,问题是双重的:为什么迈蒙尼德首先要写《指南》,而施特劳斯为什么要写深奥的著作?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施特劳斯指出,《指南》的文学形式是写给迈蒙尼德天才学生约瑟夫的一封信,约瑟夫像迈蒙尼德时代的许多犹太人一样,正在遥远的地方旅行:“约瑟夫的离开是由于他是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促使迈蒙尼德违反明确禁止[写深奥问题]的不是私人需要,而是全国范围内的迫切需要。只有拯救法律的必要性才会导致他违法”(PAW,第 49 页)。
如果这是迈蒙尼德的理由,那么施特劳斯的理由是什么?为了拯救那些秘密,施特劳斯愿意做出揭露深奥文本秘密的看似不道德和不雅的举动。施特劳斯试图拯救的秘密是洞察他所说的“一种被遗忘的写作类型”的政治、哲学和神学意义。但为什么施特劳斯关心这种被遗忘的写作类型呢?我们只能通过将施特劳斯出版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以及《迫害与写作艺术》在这整体中的位置来回答这个问题,为此,有必要理解施特劳斯最基本的问题,即他所说的“现代性的神学政治困境。”
4. 现代性的神学政治困境
在 1965 年斯宾诺莎《宗教批判》英译本的序言中,施特劳斯描述了他的思想旅程的开始,他说:“这部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研究是 1925-28 年在德国写成的。作者是一位在德国出生和长大的年轻犹太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神学政治困境”(SCR,第 1 页)。同样在 1965 年,施特劳斯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首次以德文出版,并由作者撰写了新的序言。施特劳斯在那里提到了“神学政治问题”,认为它是“我研究的主题”(GS 3,第8页)。
施特劳斯使用“神学政治困境”一词来诊断他所认为的现代早期将神学与政治分离的尝试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哲学、神学和政治后果。然而,施特劳斯绝不赞成回归神权政治,也不赞成像他同时代的卡尔·施密特那样转向政治神学。相反,施特劳斯试图恢复古典政治哲学,不是回到过去的政治结构,而是重新考虑前现代思想家认为有必要解决和忍受紧张局势的方式,如果不是矛盾的话,根据定义,这些紧张局势是由人类社会。对于施特劳斯来说,对人类社会的紧张和矛盾的认识,而不是解决,是从哲学上重建哲学、神学和温和政治的必要起点,他声称,所有这些都是二十世纪迫切需要的。需要。
5. 哲学与启示
在描述“神学政治困境”时,施特劳斯不断地回到启示相对于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地位问题。他批评从 17 世纪开始的现代宗教批判,认为它提出了启示和哲学应该符合相同科学标准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结束了对启示的有意义的讨论,或者以将启示从对话中消除的形式。或者以所谓的现代宗教辩护的形式,这种形式只会将这种放逐内在化。施特劳斯对神学政治困境的早期思考使他想到了一个他一次又一次坚持的主题:启示与哲学的不可调和性(或者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或圣经和希腊哲学的不可调和性)。施特劳斯认为,由于根据定义相信启示并不声称是不言自明的知识,因此哲学既不能反驳也不能证实启示:
真正反驳正统观念需要证明世界和人类生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不需要假设有一个神秘的上帝。它至少需要哲学体系的成功:人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表明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和自己生活的主人;仅仅给予的必须被人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创造的世界所取代(SCR,第29页)。
因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目前还不可能,所以现代哲学尽管有相反的自我理解,但并没有否认启示的可能性。
在施特劳斯的解读中,启蒙运动所谓的宗教批判最终也带来了现代理性主义的自我毁灭,而其支持者却不知道。施特劳斯并不排斥现代科学,但他确实反对“科学知识是知识的最高形式”这一哲学结论,因为这“意味着对前科学知识的贬低”。正如他所说,“科学是现代哲学或科学的成功部分,而哲学是不成功的部分——余下的部分”(JPCM,第 99 页)。施特劳斯将现代哲学史解读为以将所有知识提升为科学或理论为起点,以将所有知识贬低为历史或实践而结束。用施特劳斯的话说:“17世纪以来所有现代黑暗的根源在于模糊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区别,这种模糊首先导致实践还原为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现代] 理性主义),然后,作为报复,以实践的名义拒绝理论,而实践不再是可理解的”(FPP,第 66 页)。在十七世纪,霍布斯和他之后的斯宾诺莎一样,以科学的名义贬低前科学知识,而二十世纪的海德格尔则以历史性的名义贬低科学知识。虽然许多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解为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决裂,但施特劳斯将海德格尔的哲学视为同一理性主义的逻辑结果。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现代理性主义自我内爆:以某些知识的名义对科学标准的现代追求开始导致这样的结论:既不存在这样的标准,也不存在这样的真理。
施特劳斯认为,正如现代哲学以一种过度夸大的理性意识开始,这种理性意识将理论置于实践之上,并以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结束,这种历史主义否认历史之外的理性的任何意义,同样,现代政治哲学也开始于试图使按照科学的定义,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最终否定任何自然概念。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些轨迹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和他的政治不幸的巧合中走到了一起:
关键问题涉及人类那些永久特征的地位,例如高贵与卑贱的区别……。正是对这些永久性的蔑视,使得 1933 年最激进的历史主义者能够服从,或者更确切地说,欢迎,作为命运的安排,他的国家中最不明智和最温和的部分的裁决…… 1933 年最大的事件将是相反,似乎已经证明,如果这种证据是必要的话,人类不能放弃美好社会的问题……。 (WPP,第 26-27 页)。
施特劳斯并不是想暗示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相反,他的意思是调查为什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没有采取足够的理性、道德反应。正是在这里,现代哲学和神学危机与现代政治危机相遇。现代政治哲学、神学或哲学都没有关键资源来应对自由国家的解体,这种政治结构被吹捧为“……‘黑暗王国’的对立面,即中世纪社会的对立面”(SCR ,第 3 页)。
成熟的施特劳斯的任务是考虑哲学、神学和政治哲学如何能够再次拥有关键资源来对贵族和底层做出最基本的区分。要做到这一点,施特劳斯必须克服他所谓的“强大的偏见,即回归前现代哲学是不可能的”(SCR,第 31 页)。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际缘
- 【双男主】+【回忆杀】+【小甜饼】+【幻想】霁清轩和顾闫旭认识,相识许多年,却在结婚几年后出轨。顾闫旭在医院好似出现了幻觉,看到了18岁的霁......
- 2.0万字6个月前
- 影藏的梦
- 人类的三大情感——亲情、爱情与友情。如果有人丢失了它们,那么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毫无意识的空壳…我,四大家族之一的亚卡兰登家族中唯一存活于世的......
- 10.7万字6个月前
- 请指认我的心脏
- 简介正在更新
- 0.5万字5个月前
- Selita国度的英雄们
- 【龙偶】【自设世界观】曾经,存在着一个神奇而古老的国度,名为Selita。在这个国度里,居住着各色各样的龙,它们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宰。其中,......
- 0.6万字4个月前
- 素圈Z—12
- 特工001与实验体Z-12
- 3.2万字2个月前
- 灵感小屋的奇怪缘分
- 灵感是咕噜咕噜的泡泡,一不留神就会被小猫的爪子戳破,禾日是灵感小屋的新一任主人,透过小屋的任何东西去窥看泡泡世界的小故事。“今天…是什么呢?......
- 2.5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