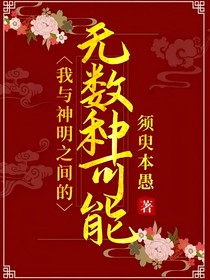法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三)
法学中的规范博物学家也以工具看待理论问题。迄今为止,从这个角度来看,证据法的哲学基础已获得最大的关注(Allen&Leiter 2001; Broughton&Leiter 2021)。正如高盛所说,我们要问:“哪种[社会]实践对知识的影响与错误和无知形成鲜明对比?” (1999,第5页)。在这方面,规范性的自然主义是逼真的(借用高盛的术语):它与知识的产生,意义(部分)真正的信念有关(Goldman 1999,第79-100页)。因此,规范自然主义者将其作为他的目标,即规范我们的认知实践的规范,以便他们产生知识。在个人认识论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管理个人应如何获得并权衡证据的规范以及最终形式的信念;在社会认识论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管理灌输信仰的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规范。反过来,法律证据规则是后者的主要案例:对于这些规则,构建了审判陪审员对事实问题的信念的认识论过程。因此,证据规则是规范博物学家进行调查的自然候选人。我们可能会要求任何特定的规则:这会增加陪审员对事实问题的真正信念的可能性吗? (当然,要求每一个规则都没有意义,因为某些证据规则(例如,联邦证据规则(fre)407-411)并不是要促进发现真理的情况,而是要执行各种政策目标,例如减少事故和避免诉讼。)这当然提出一个本质上是经验的问题:给定的证据纳入或排除规则实际上会增加事实发现者的可能性,鉴于他们实际上的样子,关于有争议的事项的知识事实(即,它是否最大化了真实价值)?当然,许多脸上的规则会邀请一种真实的分析在实践中需要一种非常不同的分析。因此,例如,FRE 404在其表面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排除了性格证据,但实际上,404(b)中的例外很大程度上吞没了规则。因此,虽然似乎我们应该询问排除角色证据是否最大化的真实价值,但真正的问题是承认它是否确实如此。传闻规则也可以这样说。尽管表面上看,传闻学是一个排斥的规则,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承认的规则:倡导者必须真正知道的是如何在名义上排斥规则的众多例外中获取供应的传闻。 (fre 802)。因此,相关的真实性问题涉及传闻所接受的理由的真实凭证,而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排除它的真实原因。 (实际上,此类问题已经是大量证据奖学金的主食。)
相比之下,在裁决理论上,规范博物学家希望确定裁决规范,以帮助法官实现裁决目标。这样的规范必须再次满足两个自然主义的约束:首先,它们必须是经验事实,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工具约束”);其次,它们必须受到有关法官性质和局限性的相关经验事实的约束(“应得的限制”(Leiter 1998)。
德沃金的裁决理论(Dworkin 1986)成为规范博物学家的流行目标。德沃金的理论非常粗略地说,法官应以这样的方式决定一个案件,以使解释先前制度历史的重要部分的原则相干,并根据政治道德的问题为这一历史提供了最佳理由。规范性博物学家可以成为迪沃尼亚人吗?
(1)工具约束:自然主义者评估规范性建议相对于其实现相关目标的实际有效性。那么,裁决的相关目标是什么?一位候选人肯定是这样:我们想给法官规范建议,以使他们达成公平或公正的结果。因此,博物学家的问题变成了:哪种规范性建议在真正帮助实际法官实现正义和公平方面最有效?至少,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否有效地领导法官做公平的事情。他的规范理论在过去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对美国司法实践的影响,这一事实至少证据表明它似乎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更不用说有效实现正义的方法了!)(Leiter 1998,1998年, p。后一点与博物学家的第二,更重要的异议有关。
(2)应该施加的限制:法官不能做的一件事是德沃金的法官赫拉克勒斯所做的。这是对Dworkin理论的熟悉的抱怨,但自然化的法学赋予了它原则上的基础。自然主义的法官避免了实际法官无法使用的所有规范指导;就像他在认识论方面的归化对应者一样,他“不想仅仅给出闲置的建议,人类(包括法官)无能为力”(Goldman 1978,第510页)。 Dworkin可能会给法官一个“有抱负的模式”(借用Jules Coleman的简短短语),而自然主义的法学则无需对此提出异议。但是笛卡尔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论上的理想模型,这并不能使他的计划更加充分或相关。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某些“清晰和独特的思想,并从中建立所有知识),那将很有吸引力。)自然主义者希望对像我们这样的生物有效的规范建议;要求法官艰苦的哲学创造性违反了这一约束。博物学家总结说,愿望并不是规范性建议的合适目的,首先,必须提供有效的目的手段。
5。实质性的自然主义
实质性的自然主义始于这样的想法,即存在自然科学的事物所描述的事物。 (物理主义,一种更严重的S-自然主义形式,认为只有物理上的事物。)这种本体论S-自然主义可能不需要,与语义S-Nataralism有关,根据此概念,必须对任何概念进行适当的哲学分析表明它可以接受经验询问。
S-自然主义在至少三种法律 - 哲学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者(例如阿尔夫·罗斯(Alf Ross)和卡尔·奥利维克罗纳(Karl Olivecrona)),他们的艰苦的自然主义与Moral Antimalism融为一体法律概念; (2)法律实证主义者,S-Nataralism可以,有时是一个重大的动机,以及(3)当代的自然法理论(例如David Brink,Michael Moore和Nicos Stavropoulos)的当代捍卫者,他援引与Kripke和Putnam相关的因果关系理论,以实质上自然主义的术语对某些法律谓词进行解释。
5.1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
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在法律哲学的其他主要传统中脱颖而出,因为法律哲学明确地将自然主义(尤其是S-自然主义)放在中心舞台上。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第二版Karl Olivecrona定律的序言中是事实,Olivecrona指出他的书的目的是“适合法律一词涵盖的复杂现象,使其成为时空世界” (1971年,第VII页)。但是,在法律和正义上的阿尔夫·罗斯(Alf Ross)(1959年,第67页;另见Spaak 2009,第40-42页)中同样重要,这可能是对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传统的国际著名贡献。鉴于S-Naturalism对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的中心地位,毫不奇怪的是,各种熟悉的自然主义动机哲学的gambits在斯堪的纳维亚主要的现实主义文本中出色。这些包括自然而然地减少法律概念的努力,以及法律话语重要方面的非认知主义和错误理论叙述。 (下面讨论了一些特定示例。)
如今,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的S-自然主义更被视为智力历史的博物馆作品,而不是在法学辩论中的现场竞争者。鉴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以及类似的乌普萨拉哲学学院对斯堪的纳维亚重大现实主义者的哲学观念和方法,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本来应该脱离青睐并不令人惊讶(Bjarup 1999,第774页;另见Sandin;另见Sandin); 1962年,第496页。尽管许多人仍然会广泛地同情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的自然主义,反文章的倾向和道德反现实主义,但总的来说,它们的特定版本并没有很好地老化。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长期接待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原因:哈特的影响(1959年)。在对罗斯关于法律和正义的有影响力的评论中,题为“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有些误导),著名地攻击了罗斯的法律哲学的核心支柱,即他对法律有效性概念的严厉自然主义分析。罗斯(Ross,1962)在他对哈特的《法律概念》的评论中做出了回应,认为哈特误解了他,他们的观点恰当地理解,并没有相距遥远。
为了了解罗斯提出的是什么,而哈特认为如此令人反感,最好从法律和正义的开篇页面开始。在那里,罗斯在两种语言含义之间进行了区分:表达和代表性。根据罗斯的说法,所有的语言话语,口头或书面都具有表达意义(即表达某些内容);但是只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含义,即代表世界上事务状态。在这里,罗斯与“我父亲死了”之类的话语进行了对比,该话语具有表达和代表性的含义,诸如“ ouch!”之类的话语与言语对比。和“关闭门”,仅具有表达意义。罗斯用代表性的话语呼唤说话,意为“断言”。没有代表性的话语,他称其为“感叹”或“指令”,如果前者不打算对他人发挥影响(例如,在反身上的“ ouch!”的情况下),那是后者,如果他们旨在发挥影响力(如“关闭门”)(1959年,第6-8页)。
罗斯认为法律规则(例如法定规定)是指令。他解释说,这样的规则并不意味着代表事态状态,而是影响行为。简而言之,如果制定法律规则,指出某些行为“应受到惩罚”或“引起责任”,那么这不是为了描述法院会做什么,而是要指导法院的行为(并间接地指导法院的行为至少,私人的行为)(1959年,第8-9页)。
那么,法律言论“在法学教科书中发生”呢?这些断言还是指令?罗斯告诉我们,在表面层面上,这样的书中的语言通常与实际法规中的语言相似甚至相同:例如,教义作者可能会说某些行为“引起责任”或“应”受到惩罚。”但是,罗斯说:“教科书中的命题在任何程度上都打算描述而不是开处方”(1959年,第9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必须是主张,而不是指令,特别是罗斯声称,关于什么是有效法律的主张。
说某事是有效的法律意味着什么?罗斯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为了预测法院的行为和思维。除了细节,要说“ X是有效的法律”实际上是说(1)法官将按照X行事,(2)这样做,他们会感到自己有必要这样做。因此,关于什么有效法律的主张是关于纯自然事件状态的主张:关于法官行为和心理的事实(1959年,第42、73-74、75页)。
Hart -Ross对话围绕着这种分析的优点;就哈特而言,他发现这完全不足。哈特(Hart)最关键而令人难忘的是,“即使在普通公民或律师的口中,这是英国法律的有效规则”,这是[英语]法官会做,说和/或感到的预测,这不可能是在没有预测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感受的法官口中的意思。”取而代之的是,这是“所讨论的规则”的“承认行为”,因为它满足了某些公认的通用标准作为系统的规则,也是法律行为标准”(1959年,第165页)。哈特(Hart)认为,罗斯(Ross)对法律有效性概念的分析失败了,因为“正常使用'法律有效'的中心用途是在一种特殊形式的内部规范陈述中”(1959年,第167页)。
后来,罗斯在对哈特的《法律概念》的评论中声称,哈特误解了他。罗斯回答说,在他对“有效法律”的分析中,他特别关注“法律概念在法律教义研究中起作用时,我们在非洲大陆上习惯了法律科学”,如果这是充分理解,很明显,他和哈特之间明显的分歧都是虚幻的(1962年,第1190页)。罗斯说,实际上,他一直在分析哈特(Hart)的法律声明,将被归类为“外部”。罗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混乱,部分原因是丹麦短语“gældenderet”为“有效的法律”,承认结果听起来是“英语用法中的奇数”,并建议通过“现有法律”或“法律”或“法律”有效”可能会更好地抓住他的想法。 (有关翻译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Eng 2011。)
随后重新审视Hart -Ross辩论的许多作者对Ross的说法被误解了。 (请参阅Pattaro 2009,第545-546页; Eng 2011; Holtermann 2014,第166页。4。)尽管如此,就智力史而言,Hart的批评具有其作用。但是,最近对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的兴趣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对法律哲学中自然主义的更广泛的兴趣。
这并不局限于严格的历史或释经工作,还包括努力挖掘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的著作,寻找可能有助于推进当代法律哲学的哲学策略或见解,或对其思想进行富有成效的理性重建。 (参见 Holtermann 2014;Spaak 2014,第 10 章。)
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可能感兴趣的一些当代兴趣主题之一是用表现主义和/或非认知主义术语理解法律语言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由于凯文·托(Kevin Toh)在该主题上的工作,最近人们对法律(或“元法律”)表现主义产生了一些兴趣,即将法律陈述视为独特(也许是意动)心理状态的表达。 (参见Toh 2005;Toh 2011;Etchemendy 2016。)鉴于非认知主义思想在其法律语言理论中的突出地位,当代法律表现主义者可能将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视为某种知识的先驱。
众所周知,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是伦理非认知主义者。 (Bjarup 1999,第 775 页;Ross 1959,第 313 页;Spaak 2009,第 42-44、52-55、64 页。)原则上,这不需要对法律陈述采用表现主义或非认知主义解释,但碰巧罗斯和奥利弗克罗纳确实理解有关该模式的法律论述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肯定的是,罗斯将有关“有效法律”的陈述分析为自然主义事实的断言,因此也是认知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罗斯认为一些法律话语是非认知指令。这最明显包括法律规则本身,如法规的规定。但罗斯也认为法学家的理论著作通常是有效法律的认知断言和非认知指令的混合体,后者实际上是旨在影响司法机构行为的建议(1959,第46-49页)。在提出这一想法时,罗斯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陈词滥调的观点,即教义写作中经常夹杂着关于法院应如何裁决案件的明显规范性主张。他的观点比这更微妙。罗斯的观察结果是,教义作者有时确实(有时有意)通过做出表面上同样可以被解释为直接预测/描述性主张的陈述来影响法官。因此,事实证明,罗斯对法律话语中认知(或代表性/描述性)和非认知(或指令性/规定性)元素的混合有相当细致的理解。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非认知主义思想在奥利弗克罗纳成熟的法律哲学中发挥着更加引人注目的作用,特别是在《法律即事实》第二版中阐述的那样。奥利弗克罗纳对减少对自然主义事态主张的合法权利的讨论感到不满意,他最终得出结论,常用的“权利”一词没有任何意义,并且缺乏语义参考(1971,第183-184页)。他认为,首先,有关合法权利的陈述具有指导功能,尽管它们也可以间接地传达有关实际(自然)事实的信息。最终,奥利弗克罗纳将这种分析扩展到一般的法律语言,并得出结论:“法律语言不是描述性语言。它是一种指导性的、有影响力的语言,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1971,第253页)。为了避免人们对奥利弗克罗纳的这一想法的理解程度产生怀疑,他继续指出,根据他的说法,“公民、政府、议会、法律、权利、义务、婚姻、选举、税收、公司和公主都属于[ e]“……缺乏语义参考的单词”的类别(1971,第 255 页)。因此,奥利弗克罗纳在他作为 S 自然主义者所承认的事实世界中,找不到法律语言表面上“有关”的许多“事物”的位置。然而,正如在某些思想和谈话领域拥护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经常发生的那样,奥利弗克罗纳同样坚持认为法律语言和思想确实在现实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因此,他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描述法律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最终得出结论,“法律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了维持和平,以及派遣人们去执行任务”。战场上的死亡”(1971,第 254 页)。因此,只要当代对法律思想和谈话的表现主义和/或非认知主义解释有一些兴趣,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可能会为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趣的思想历史参考点(可能还有实质性的灵感)。
5.2 法律实证主义
至少在当代英美法哲学中,“法律实证主义”通常被用作大致如下主张的简写:“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取决于社会事实,而不是其优点”(Green 2009)在上述意义上,自然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情况有些复杂,因为一些但并非全部法律实证主义者都是自然主义者,而且很少有人能像斯堪的纳维亚现实主义者那样将自然主义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然而,简而言之,自然主义有时能够——但不一定——在推动法律实证主义方面发挥作用。
自然主义如何在推动法律实证主义方面发挥作用?正如人们经常评论的那样,实证主义关于法律与社会事实之间关系的核心主张实际上相当于一种主张,即法律可以还原为社会事实,考虑到此处的“社会事实”,默认情况下(如果不是明确的)仅限于心理和社会学事实——进一步等于法律可以还原为自然主义事实的主张。应该很清楚为什么这会吸引那些具有 S 自然主义承诺的人,因为可以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法律“放置”在自然主义事实和实体的领域中。 (通过类比,考虑一下为什么 S 自然主义者会被这样一种观点所吸引,即人类思想的存在和内容完全取决于人类大脑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法律实证主义和 S 自然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没有被忽视。 (参见 Kar 2006,第 931 页;Leiter 2018,第 19-20 页。)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丧尸界里当军师
- 1V1四对cp凌芊芊从小与他人不同一次她跟随老奶奶进入另一个异空间。当起了界丧尸家族的国师。开启国师之路,慢慢的自己的身世之谜浮出水面知晓自......
- 23.6万字5个月前
- 我与神明之间的无数种可能
- 【双向暗恋+一见钟情】都说神明普度天下,潞鸢却不赞同。初入九重天,潞鸢带着灭族之痛,一腔怒火,此生只为手刃仇人与神明。再入九重天,他带着身后......
- 10.8万字3个月前
- 长夜的消散
- 白色的风筝也要独属于它的夜晚
- 0.2万字3个月前
- 复仇:命运挽杀
- “杀手的复仇,才刚刚开始。”-林怀雾“一刻之仇,一生莫忘。”-林怀尘“我的复仇,可没有那么简单。”-林思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林思星杀......
- 0.7万字3个月前
- 奇思妙想,各种各类小说合集
- 此文不只有一个故事,很多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短篇小说。第一篇:花心痞帅硬汉;季北辰VS独立理智坚韧冷艳美女;莫希。(现代言情,花心浪子遇真爱......
- 4.2万字2个月前
- 泰版流星花园:奇妙的邂逅
- 【2025.3.6完结】女主有一个奇妙的能力,就是变成一个胖嘟嘟的,可可爱爱的小女孩。女主通过变成小女孩来作弄f4,后来被Ren发现身份........
- 6.7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