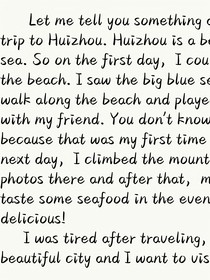铁莲花(一九六六年冬)
雪是红的。
林红梅跪在诊所天井的青砖上,唾沫混着冰碴砸在脊梁骨,烫出一串燎泡。红卫兵小将用皮带扣抽她后颈,铜扣上“为人民服务”的阳文嵌进皮肉,血珠滚落时在地面拼出“反动医霸”的草书。她数着砖缝里的蚂蚁—第七只缺了左触须,和青山被押走那日药箱里爬出的一模一样。
黑猫蹲在批斗台横幅上,瘸腿缠着褪色的红袖章。它的右眼珠被挖去,空眼眶里塞着团锈铁丝,铁丝末端连着高音喇叭的电路。每当有人喊“打倒”,猫喉管就爆出电流杂音,像是青河在哼《东方红》。
“坦白从宽!”红卫兵队长踹翻药柜,艾绒与砒霜粉扬成灰雾。红梅盯着滚到脚边的针灸盒,檀木盖裂了条缝,露出里面菌丝缠裹的银针—那是养母临终前泡在药酒缸里传下的,针尾缀着观音土烧的瓷珠,遇血即裂,渗出樟脑味的黑汁。
第一个患者是半夜翻墙进来的。
男人左胸别着主席像章,右脸被烙铁烫出“叛徒”二字,溃烂的皮肉里钻出细白菌丝,随心跳忽明忽暗。红梅认出他是县医院的李院长,去年带头砸了祖传药箱。“救我…”他掀开棉袄,肚脐眼长出朵铁皮焊的莲花,莲心嵌着青山的半框眼镜,镜片裂成蛛网状。
针灸盒在煤油灯下泛出尸绿。红梅抽出最长那根菌丝银针,针尖挑破铁莲花瓣,脓血喷溅在主席像章上,蚀出个骷髅轮廓。李院长突然抽搐,菌丝从眼眶钻出,在空中扭成日文“実 ”的片假名。黑猫从梁上扑下,独眼映出青山在实验室往青河脊柱注菌液的画面,针管刻度是血写的“忠”字。
“反革命医疗黑线!”红卫兵破门而入时,红梅正将银针刺入李院长的百会穴。菌丝顺针管爬进她指缝,在皮下拼出满洲地图的血管纹路。皮带扣抽在肩胛骨上的瞬间,她听见青河在药酒缸里拍打菌膜,声波震碎了三里外的烈士纪念碑。
游街那天,铁莲花开了。
红梅颈挂破鞋,菌丝从针灸盒缝隙钻出,缠住铜锣的槌头。每敲一声锣,铁莲花就绽开一瓣,莲心吐出微型胶卷的碎片。黑猫跟在牛车后,瘸腿的伤口甩出荧蓝血珠,落地即长成带刺的语录标语。路过的孩童捡起胶卷对日光照,显影的却是青山穿着白大褂解剖活人的连环画,每帧右下角都印着“仁心堂监制”。
地窖成了临时手术室。
红梅用菌丝缝合被批斗者的伤口,菌群在血肉间分泌镇痛黏液,结成半透明的语录膜。深夜总有戴纸帽的干部爬进来,他们剖开左胸露出心脏,心尖上长着铁蒺藜,刺间缠满青河实验报告的残页。红梅以银针挑刺,铁蒺藜遇菌即溶,渗出墨汁写就的认罪书。
冬至夜,黑猫产下一窝铁崽。
幼崽通体冰凉,眼珠是砒霜结晶,哭声像高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红梅将它们浸入药酒缸,缸底沉着青山的钢笔,笔尖涌出菌丝填满幼崽七窍。酒液沸腾时,铁崽融化重组,凝成一尊挥手像,掌心纹路拼出青河的绝笔:“哥,我成了你的手术刀。”
最烈的批斗在小年夜。
红卫兵将红梅绑在诊所门柱,用烧红的银针烙她乳房。“正好治乳腺增生。”她笑出声,焦糊味引来大群萤火虫,虫腹闪着“孝”字绿光。黑猫蹿上房梁扯断电线,电火花引燃菌丝银针,火舌舔过针灸盒,檀木盖内浮现青山解剖青河的手记:“四月七日子时,剥离第49号实验体翅膀,制成六盏菌灯,献予军部庆贺天皇生辰。”
暴雪压垮诊所房梁时,红梅挣脱绳索爬向地窖。
菌丝银针在掌心熔成铁水,滴落处地砖浮现满洲铁路路线图。黑猫叼来半片胎盘—泡在药酒缸三十年的青河遗物,胎盘血管凸起如活蛇,缠住红梅脚踝将她拖向菌丝最密的墙角。菌群裹住她躯干的刹那,红卫兵冲进来,手电筒光柱里,她正蜕去人皮,新生的菌膜表面浮出青山的脸。
“妖婆现形了!”
锄头砸在菌膜上进出蓝火,火中传出青河被注射菌液时的惨叫。红梅的残躯在菌丝间游走,断指蘸血在墙面书写:“救人是罪,杀人成佛。”黑猫跃入火海,瘸腿的铁骨熔成主席像章,扣在红卫兵队长的左胸,烙出“医”字篆印。
清尸时发现地窖暗门。
红梅的针灸盒躺在青河药酒缸旁,菌丝已爬满盒内银针,针尾瓷珠碎裂处露出微型胶卷。红卫兵展开胶卷,显影的却是林沉在2010年焚烧诊所的远景,火光中飘着张未燃尽的处方笺,背面有行褪色血书:“爹,我接住了你断指发的芽。”
开春时,铁莲花的种子随风扩散。
患者从咳出铁屑到内脏钙化,死时通体冰凉如手术器械。红卫兵队长死前攥着那枚“医”字像章,医护人员剖开他心脏,发现瓣膜上刻着青山的手迹:“昭和二十一年四月七日,弟青河停止呼吸,菌灯亮度达三千支烛光,谨以此光耀天皇圣战。”
黑猫的幽灵在诊所废墟徘徊。
它独眼换成了解放帽徽,瘸腿缠的菌丝正缓缓拼出林建军的面容—那个在改革年代倒卖器官的养子,此刻正在母胎中吸收红梅的菌血,准备降临这个需要铁与火接生的世界。
我在诊所的那些年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第六学院(乱穿越的家伙们都是项链惹的祸当然作者也在内)
- 讲述的是来自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聚集在一所平凡又不是平凡的学院中就是第六学院………
- 3.4万字10个月前
- 超兽武装:圣界龙祖,雪皇护道人
- 龙彻穿越到超兽武装的世界,拜了一个神秘人为师…然后短短10万年,他就成为了七天平行宇宙的最强,被尊为圣界第一强者,老雪皇死后,他就权倾第七平......
- 新书6个月前
- 西克的异界游行
- 作者的想象力丰富但有限,可以在评论区出点子改剧情,谁的能选上就得看作者的心情喽!
- 0.7万字6个月前
- 吃瓜群众,在线粮仓
- 【知道四大美女,但你知道四大丑女四大丑男吗?想知道两面宿傩的传说吗?你赶五穷了吗?……】1.为本人各种类型文字收集册,请一定要观看分卷简介,......
- 4.2万字5个月前
- 局中迷,观者清
- 人物性格不一,各怀鬼胎,棋盘之上,是局中人还是观棋者...
- 0.3万字5个月前
- 解锁系统:承受痛苦
- 林泽恩解锁了共享痛苦系统
- 1.2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