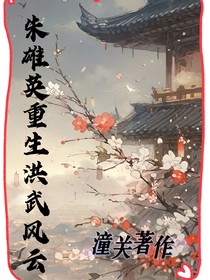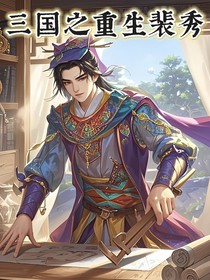第二章 三岁的算学游戏
大楚永熙二十年谷雨,定国公府东跨院的樱花正落。三岁的萧文远蹲在青石路上,手里攥着半块芝麻糖,盯着面前排成一列的糖葫芦发呆——这是他用祖父给的玉佩,从厨房刘嬷嬷那里换来的“算学道具”。
“哥儿又在摆弄糖葫芦?”乳母王嬷嬷端着杏仁酪走来,见他把山楂果按大小排成三列,最小的那串只剩三颗果子,“当心夫人瞧见,又要说你糟践吃食。”
文远头也不抬,小手指点着最大的那串:“这串七个果,中串五个,小串三个,一共十五个。刘嬷嬷说三个铜板一串,总共……”他掰着沾满糖渣的手指算了算,突然眼睛一亮,“九个铜板!比买整串便宜一个铜板呢!”
话音未落,忽听得游廊传来脚步声。十五岁的萧文昭穿着新制的黛青劲装,腰间玉佩穗子换成了耐磨的棉线——自去年被弟弟攥坏后,他便特意换了结实的绳结。
“文远,”萧文昭在廊柱后顿住,耳尖微微发红,“今日随我去演武场,教你认弓箭。”
文远立刻把糖葫芦往背后藏,糖渣撒了满地:“兄长昨日说认弓箭,结果让我举着木弓站了半个时辰!”他忽然瞥见萧文昭袖口露出的油纸包,眼睛一亮,“兄长又带了蜜饯?给我一块,我便乖乖去。”
萧文昭无奈地叹气,将油纸包扔过去:“下不为例。”看着弟弟蹲在樱花树下拆包装,他忽然想起去年抓周时,那只攥着蜜饯不松手的小肉手——如今这双手,既能拨弄算盘,也能把糖葫芦摆成算筹。
正闹着,月洞门处传来通报:“老国公到!”
文远立刻跳起来,拍了拍沾满糖渣的衣袖。老国公萧定山拄着龙头拐杖走来,虎皮大氅换成了轻便的青竹纹夹袄,腰间别着个新打的小算盘——这是他特意让铁匠铺打的,专为给孙子当玩具。
“小崽子在摆弄什么?”老国公弯腰捡起地上的糖葫芦,见上面的山楂果被摆成算筹形状,忽然大笑,“好!比你兄长当年拿箭杆算数目强多了。”他从袖口摸出个青铜小酒壶,晃了晃,“祖父今日教你算酒账如何?”
文远眼睛一亮,立刻拽着老国公的衣袖往石桌跑:“要算祖父的藏酒!上次库房清点,您偷偷藏了三坛二十年的女儿红!”
萧文昭在旁摇头失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笑声。转身只见妹妹萧文缨躲在假山后,发间别着朵歪歪扭扭的樱花,裙摆上绣的小老虎被她自己添了条夸张的尾巴——这是她昨日趁母亲午睡时,用朱砂笔偷偷画的。
“五哥又在偷懒!”文缨跑出来,举着根竹枝当马鞭,“昨日先生教的《三字经》,你是不是又没背?”
文远吐了吐舌头,躲到老国公背后:“祖父说,会算酒账比背《三字经》有用。”他忽然看见文缨腰间挂着的琉璃铃铛,眼睛一转,“妹妹帮我打掩护,明日分你半块奶油酥如何?”
老国公坐在石桌旁,看着两个孙辈追跑打闹,手中的小算盘拨得哗啦响。阳光穿过樱花树,在文远月白长衫上洒下斑驳光影,袖口的糖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孩子,总把日子过成甜丝丝的算学游戏。
申时三刻,世子夫人李氏带着丫鬟寻来,见儿子正趴在石桌上画算盘,老国公在旁用酒壶当镇纸,案头散落着沾着糖渍的草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酒三坛,坛七升,共二十一升”。
“又跟着祖父胡闹,”李氏笑着刮了刮文远的鼻尖,“明日随我去佛堂抄经,免得你把算学用到藏酒上。”
文远苦着脸抱住老国公的胳膊:“母亲~抄经不如算经有趣……”话未说完,忽然看见李氏手中的食盒,眼睛立刻亮起来,“是新做的蟹粉豆腐羹?我能边吃边算经吗?”
老国公哈哈大笑,拍了拍孙子的小肩膀:“瞧瞧,这才是我萧家的算账奇才。将来啊,定能把库房的酒账算得明明白白,让你父亲再也抓不到祖父藏酒的把柄!”
暮色漫进院子时,文远趴在乳母肩头打盹,小嘴里还嘟囔着“三坛酒二十一升”。萧文昭收拾石桌上的算筹,发现弟弟用糖葫芦摆的算式旁,画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旁边写着“兄长的蜜饯甜,祖父的酒坛多”——虽不成字,却让少年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这一晚,定国公府的演武场上,萧文昭对着月光擦拭长剑,忽然想起白日里弟弟算酒账时的认真模样。他忽然明白,有些成长不必在演武场,有些担当也不必在沙场——只要这孩子能在算珠与甜点间找到自己的天地,便是定国公府最大的福气。
樱花树下,老国公的小算盘还在石桌上,一颗滚落的山楂果停在算珠旁,像极了三年前抓周时那粒沾着糖霜的蜜饯。命运的轨迹,正以最甜美的方式,在这个被全家宠爱的小公子脚下,铺就一条独特的人生路。
定国公府二公子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CH:社会主义三部曲
- (各位审核大爹,不要屏蔽我的书,我只想让更多人了解历史,政治敏感话题我会尽量回避)以同人文的形式展示二战后三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纯历史向没......
- 0.7万字6个月前
- 风萧亦寒(姒黎)
- 女性不比男性差,华夏将永远昌平
- 0.1万字3个月前
- 朱雄英重生之洪武凤云
- 2.6万字2个月前
- 三国之重生裴秀
- 不太会写
- 0.9万字2个月前
- 战国千年
- 如果长平之战秦赵双方平手,秦始皇被刺杀成功,战国时代继续,天下大乱。各路英雄争相崛起,华夏文明又将走向何方
- 2.6万字1个月前
- 历史小说集
- 以虚构的故事回顾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加以反思,铭记当今世界和平的不易,顺便磕一下每个国家之间的CP
- 0.9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