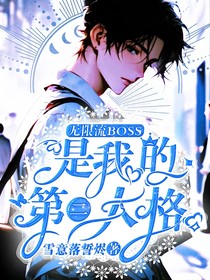逆袭皇子
王侍卫的消息递回来时,是个微雨的清晨。他揣着个油纸包,瘸着腿钻进草屋,裤脚沾满泥点,进门就压低声音:“殿下,您猜得没错!户部侍郎李嵩这几日确实在查漕运,听说还扣了一批江南来的官粮,跟漕运总督吵得不可开交!”
萧然正蹲在灶台前生火,火苗舔着潮湿的柴禾,发出噼啪的轻响。他闻言抬眸,眼底映着跳跃的火光,亮得惊人:“吵得有多凶?”
“听说在总督府拍了桌子!”王侍卫解开油纸包,里面是两个温热的肉包子,是他用半个月的工钱换的,“码头的力夫说,李侍郎放了狠话,要参漕运总督一本,说他勾结商户、倒卖官粮。”
萧然接过包子,指尖触到温热的油皮,忽然笑了:“勾结商户?这罪名可不小。”他掰了半只包子递给王侍卫,“李嵩是新帝的心腹,漕运总督却是先皇旧部。新帝登基后,一直想把漕运这块肥肉收回来,李嵩这是在替主子出头呢。”
王侍卫啃着包子,含糊道:“那咱们……”
“咱们?”萧然咬了口包子,肉馅的鲜香混着葱香在舌尖散开,他细细品了品,才慢悠悠道,“咱们去给漕运总督‘报个信’。”
王侍卫愣住:“报信?咱们怎么进总督府?再说了,那总督大人能信咱们?”
“进不去,不代表传不到话。”萧然起身,走到墙角翻出件相对干净的粗麻衣,又从灶膛里捻了点草木灰,往脸上抹了抹——这是他这些日子摸索出的“伪装术”,灰头土脸能遮住大半容貌,却独独留着双清亮的眼睛,显得既怯懦又无辜。
“您这是要……”
“去总督府附近的茶馆坐坐。”萧然拍了拍王侍卫的肩,“记住,待会儿看到穿藏青色官服、腰间挂着玉牌的人,就往他身边‘撞’一下。”
半个时辰后,总督府斜对面的“迎客茶馆”里,萧然缩在角落的桌子旁,面前摆着一碗最便宜的粗茶。茶馆里人来人往,大多是等着给总督府递帖子的官员随从,说话都压着嗓子,透着股官场特有的谨慎。
他刚抿了口茶,就见王侍卫一瘸一拐地从门外进来。王侍卫眼神扫过全场,很快锁定了窗边一个中年男人——那人穿着藏青色常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白玉牌,正是总督府的幕僚长张启。
王侍卫深吸口气,故意脚下一滑,“哎哟”一声撞在张启的桌角,手里的空茶碗“哐当”落地,摔得粉碎。
“你这人怎么走路的?”张启皱眉,刚要发作,却见王侍卫慌忙跪下磕头,手忙脚乱间,一张揉皱的纸条从袖管滑出来,刚好落在张启的靴边。
“小人该死!小人不是故意的!”王侍卫头也不敢抬,连滚带爬地往外跑,路过萧然身边时,飞快地眨了眨眼。
张启盯着地上的纸条,又看了眼王侍卫消失的方向,眉头皱得更紧。他不动声色地用脚把纸条勾到桌下,指尖夹起纸条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炭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急切:
“李侍郎藏了账册在城西粮仓,今夜三更。”
张启的瞳孔微缩。他伺候漕运总督多年,自然知道李嵩查漕运是假,想搜出当年总督与先皇往来的密信是真。那些信若被搜走,扣个“私通废太子”的罪名,总督府上下都得掉脑袋!
他捏紧纸条,余光下意识扫过茶馆。角落里那个灰头土脸的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少年正低头喝茶,侧脸沾着灰,可抬眼时,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含着两汪清泉,与这市井茶馆格格不入。
少年似是察觉到他的目光,慌忙低下头,肩膀微微发颤,活脱脱一副被官爷吓到的样子。
张启收回目光,将纸条揉成粉末。不管是谁递的消息,宁可信其有。他起身结账,脚步匆匆地往总督府走。
茶馆角落里,萧然看着他的背影,端起茶碗,轻轻吹了吹浮沫。碗沿映出他眼底的笑意,快得像水面的涟漪。
“系统,看到了吗?”他在心里说,“不用花钱,不用托关系,一个眼神,一张纸条,就能让总督府的人替咱们跑腿。”
系统嗤笑:“侥幸罢了。要是张启没看见纸条,或者直接把王侍卫当刺客抓了,你哭都来不及。”
“所以才要算准时机。”萧然放下茶碗,碗底与桌面碰撞,发出轻响,“张启是幕僚长,最擅长察言观色。王侍卫的‘慌张’和‘笨拙’,反而像极了被吓坏的信使。至于纸条……”他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藏青色官服配白玉牌,全京城都知道是总督府的人,王侍卫‘撞’得那么准,他能不多想?”
系统没话说了,半晌才憋出句:“你这心眼,比筛子还多。”
傍晚时分,消息就传了回来。王侍卫气喘吁吁地跑进门,脸上带着难以置信的兴奋:“殿下!成了!总督府的人傍晚时分突然查封了城西粮仓,听说从地窖里搜出了好几箱账册,还抓了李侍郎派去看守的人!现在整个京城都在传,李侍郎私藏漕运黑账,想栽赃给总督大人呢!”
萧然正在灯下翻着王侍卫找来的旧书,闻言只是淡淡“嗯”了一声,指尖在泛黄的书页上划过,停在“漕运赋税”几个字上。
“李嵩不会善罢甘休的。”他头也不抬,“他是新帝的心腹,被当众打脸,肯定会反扑。”
“那咱们……”
“咱们等着。”萧然合上书,烛火在他眼底跳动,“等张启来找咱们。”
果然,第二天清晨,一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悄悄摸到了贫民窟,找到王侍卫,只丢下一句“我家主子有请”,就转身消失在巷口。
萧然换了身干净的粗麻衣,没再往脸上抹灰,只让王侍卫用布带缠了缠他胳膊上的旧伤——那道疤如今成了最好的“身份证明”,证明他确实是那个“受尽欺凌”的落魄皇子。
跟着汉子穿过三条街,绕进一处隐蔽的宅院。院里种着几株玉兰,花瓣上还沾着露水,与外面的市井喧嚣仿佛两个世界。张启正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喝茶,见萧然进来,眼神暗了暗。
眼前的少年比茶馆里看到的更清俊,粗布衣服穿在他身上,竟穿出了几分清雅。尤其是那双眼睛,明明年纪不大,却沉静得像深潭,让人看不透深浅。
“阁下就是给总督府递信的人?”张启放下茶杯,开门见山,“不知三殿下……找老夫有何吩咐?”
他直接点破身份,显然早已查清萧然的底细。
萧然没慌,反而学着市井少年的样子,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声音放得很轻,却字字清晰:“小子不敢称‘殿下’,只是想求张大人指条活路。”
“活路?”张启挑眉,“三殿下如今虽落魄,却也是皇家血脉,怎会需要老夫指活路?”
“皇家血脉?”萧然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阴影,语气带着点自嘲,“新帝登基,第一道旨就废了我的身份。如今在京城,人人都能踩我一脚,张大人觉得,这样的‘血脉’,能活多久?”
他抬起头,眼底闪过一丝恰到好处的脆弱,却又很快被倔强取代:“小子知道,李侍郎倒台,总督大人暂时安全了。可新帝若想再找由头,总有办法。小子不敢奢求别的,只想找个地方安身,若将来能帮上总督大人一二……也算报答今日收留之恩。”
这番话,既放低了姿态,又隐隐透出“我有利用价值”的信号。张启看着他,忽然笑了:“殿下倒是坦诚。只是……老夫凭什么信你?”
萧然从怀里摸出块东西,轻轻放在桌上。那是半块玉佩,边角已经磨损,玉质却温润,上面刻着个模糊的“珩”字——是原主生母留下的唯一遗物,比木牌更能证明身份。
“这是先皇赐给母妃的,母妃临终前给了我。”他指尖摩挲着玉佩,声音低了些,“张大人若不信,可拿去验。”
张启拿起玉佩,对着光看了看,又摸了摸上面的刻痕,半晌才放下:“殿下想如何安身?”
“小子想读书。”萧然抬眸,眼里闪着光,“读史书,读律法,读那些能让我看懂这京城风云的书。”他顿了顿,补充道,“不用总督府出银子,小子可以去书铺打杂,只求能蹭着看书。”
张启沉默片刻,忽然笑了:“总督大人说,殿下是个聪明人。看来,他没看错。”他起身,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递给萧然,“这些先拿去看。书铺的事,老夫会安排。”
走出宅院时,阳光刚好越过墙头,落在萧然手里的书上。书页崭新,还带着墨香。王侍卫跟在他身后,激动得说不出话。
“看见了吗?”萧然低头翻着书,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这就是‘借力’。不用硬碰硬,只用一张纸条,半块玉佩,就能换来读书的机会。”
系统在他脑海里哼了一声:“得意什么?这才只是开始。等你真要跟新帝对上,有你受的。”
“急什么。”萧然合上书,阳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双眼睛映得格外亮,“路要一步一步走,书要一页一页读。”他掂了掂手里的书,像是在掂量分量,“至少现在,咱们不再是只能在贫民窟劈柴的废物了,不是吗?”
王侍卫用力点头,看着自家殿下的背影,忽然觉得,这清瘦的少年身上,好像真的藏着能掀翻风云的力量。
而萧然走在阳光下,指尖划过书脊,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下一个,该轮到谁了?
书铺的差事是张启托人安排的,在城南的“文渊阁”。掌柜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头,姓周,据说曾在翰林院当过低阶编修,因得罪权贵才被贬斥,开了这家书铺糊口。
萧然第一天去上工时,穿了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是张启让人送来的,浆洗得笔挺,衬得他本就清俊的眉眼愈发斯文。周掌柜坐在柜台后翻账本,抬眼瞥了他一下,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审视:“张大人说你想看书?”
“是。”萧然躬身行礼,动作标准得像模像样,“晚辈赵珩,不求工钱,只求能在打杂之余,借贵铺的书读一读。”
周掌柜放下账本,敲了敲柜台:“先试试吧。把东墙那摞《论语》搬到后堂去,动作轻点,别磕坏了边角。”
那摞书足有半人高,纸页泛黄却平整,显然是精心保存过的。萧然伸手去搬,指节微微用力——这具身体虽孱弱,但他早已摸清了发力的诀窍,看似轻松地将书摞抱起,脚步稳当得没让书页晃出半分。
周掌柜的目光在他背影上多停留了片刻。
文渊阁的日子过得规律。清晨洒扫,白日里整理书架、登记新书、帮客人找书,傍晚关门前再把散落的书卷归位。萧然手脚麻利,记性又好,不过三日,就把铺子里几千册书的位置记了个全。客人要找某卷某章,他总能精准地从书架深处抽出来,连周掌柜都忍不住赞一句“伶俐”。
但真正让周掌柜另眼相看的,是第五日午后。
那天来了个穿锦袍的公子哥,带着两个随从,进门就嚷嚷着要找《南疆异物志》。周掌柜皱了皱眉:“那书是孤本,不外借。”
“谁要借?”公子哥嗤笑一声,随手扔出一锭银子,“我买了。”
周掌柜脸色沉了:“本店不卖孤本。”
“你知道我是谁吗?”公子哥挑眉,“我爹是礼部尚书!别说一本破书,就是你这铺子,我想要也能……”
话没说完,就被一个清润的声音打断:“公子怕是记错了,《南疆异物志》并非孤本。”
萧然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手里捧着一卷书,正是那公子哥要找的《南疆异物志》。他将书卷放在柜台上,指尖点着扉页的印章:“这卷是手抄本,原书藏在皇家秘阁,据说当年南疆献书时,除了给朝廷的正本,还送了副本给靖安侯府。”
公子哥愣了愣:“靖安侯府?”
“正是。”萧然微微一笑,“侯府世子与公子同科进学,公子若去借,想必不难。而且……”他话锋一转,声音压低了些,“手抄本错漏颇多,比如第三章写‘人面蛛喜食人肉’,其实是误传,真正的记载是‘喜食蜂蛹’,公子若拿着这卷书去研究,怕是会闹笑话。”
公子哥的脸瞬间涨红,看看萧然,又看看周掌柜,哼了一声,带着随从灰溜溜地走了。
周掌柜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看向萧然的眼神多了几分探究:“你怎么知道这些?”
“以前在宫里,听老太监提过几句。”萧然垂眸,掩去眼底的精光——这些都是他从张启给的书里看来的,再结合原主零碎的记忆拼凑而成,“侥幸记下来了。”
周掌柜没再追问,只是淡淡道:“后院有间空房,你今晚起就住那吧。”
住进书铺的第一晚,萧然在灯下翻完了《南疆异物志》。系统在他脑海里打哈欠:“你看这些杂书有什么用?还不如让我帮你查新帝的弱点,早点完成任务。”
“查一次多少‘力’?”萧然头也不抬。
系统噎了下:“……五百。”
“告辞。”萧然翻过一页,“我宁愿自己找。”他指尖划过书页上关于南疆毒物的记载,忽然笑了,“你看这段,‘金蚕蛊需以活人精血喂养’,像不像某些总想着吸我灵魂之力的东西?”
系统气炸:“你才是蛊!你全家都是蛊!”
萧然低笑出声,很快又敛了笑意。他从怀里摸出张纸条,上面是王侍卫刚送来的消息——李嵩被漕运总督反参后,新帝虽没治他的罪,却把他调离了户部,改任闲职。如今户部尚书的位置空着,好几位官员都在盯着。
“机会来了。”萧然指尖在“户部尚书”四个字上轻轻敲了敲。
接下来几日,萧然白天在书铺打杂,晚上就借着整理旧书的由头,翻遍了库房里的地方志和官员奏议。他发现,近三年来,江南水灾频发,可朝廷拨下的赈灾款却屡屡“失踪”,负责督办此事的,正是现在盯着户部尚书位置的礼部侍郎。
这天傍晚,张启的人又来了,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张银票,五十两,还有张字条:“总督谢殿下援手,此为薄礼。”
萧然把银票还给来人:“替我谢总督大人,心意领了。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银子。”他顿了顿,补充道,“帮我带句话给张大人,就说江南的账本,或许比户部的账本更有意思。”
来人走后,系统啧啧称奇:“放着银子不要?你转性了?”
“银子会花完,但消息不会。”萧然拿起那本记载江南水灾的地方志,指尖划过“淮安府”三个字,“五十两,换一个让礼部侍郎睡不着觉的消息,很划算。”
三日后,淮安府知府突然上奏,说当年的赈灾款被人挪用,还附了份详细的账目,直指礼部侍郎。新帝震怒,当即下令彻查,礼部侍郎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争户部尚书的位置?
消息传到书铺时,周掌柜正在教萧然拓印古籍。他看着萧然将宣纸铺在石碑上,动作轻柔却稳当,拓出来的字迹清晰工整,竟比他这老手还像样。
“听说了吗?礼部侍郎被查了。”周掌柜忽然开口。
“嗯,听客人提了句。”萧然将拓片揭下来,晾在一旁,“世事难料。”
“你觉得,下一个会是谁?”周掌柜问。
萧然抬眸,对上老人探究的目光,笑了笑:“谁贪心,就该是谁。”
周掌柜深深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前堂。
萧然看着手里的拓片,眼底的笑意渐渐淡去。他知道,周掌柜已经猜到了些什么。但这老头曾在官场打滚,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留着他,或许比赶走他更有用。
入夜后,张启亲自来了。他带来一坛酒,还有几碟小菜,与萧然在后院对坐。
“殿下这步棋,走得妙。”张启倒了杯酒,推到萧然面前,“现在户部尚书的位置,总督大人的人有机会了。”
“不是我的棋,是张大人的。”萧然端起酒杯,却没喝,“我只是恰好知道些消息。”
张启笑了:“殿下不必谦虚。说吧,这次想要什么?”
“我想借《永乐大典》看看。”萧然直视着他,“特别是关于漕运改制的部分。”
张启的笑容僵了下:“那书在皇家秘阁,除非……”
“除非有官员举荐。”萧然接话,“周掌柜曾在翰林院任职,若他肯举荐我去秘阁抄书,应该可行。”
张启沉默片刻,点了点头:“我去说。”
送走张启,萧然站在院里,看着月亮在云层里穿梭。系统在他脑海里哼道:“你这是得寸进尺。皇家秘阁是那么好进的?”
“不好进,才值得去。”萧然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玉兰花瓣,“那里藏着的,可不止是书。”
他知道,自己离那个王位,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每一步,他都踩得很稳。从贫民窟的草屋,到书铺的后院,再到即将踏入的皇家秘阁,他像一株在石缝里生长的植物,悄无声息,却韧劲十足。
而那些曾经轻视他、欺辱他的人,还不知道,这株看似柔弱的植物,早已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伸出了藤蔓,正一点点缠绕上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之树。
月光洒在萧然脸上,映出他清俊的眉眼,也映出那双眸子里,越来越深的算计与锋芒。
神明未故-d873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凌安诺
- 一位是清冷的大师兄,一位是皎皎如月的小师妹,他们是人人称赞的模范夫妻……只是小师妹消声灭迹,寻不到人影。大师兄身负重伤,昏迷不醒……
- 0.7万字10个月前
- 杂篇论(随笔)
- 时不时的构思,更新全看心情,是的,我就是这么懒(划掉)随意~
- 0.8万字10个月前
- 明暗交响
- 她,曾经是大陆的魔女,人们说她残害亲眷,阴险狠毒,为楚家之耻。最后,她死于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之手。后来,她重生,伪装,复仇。假扮学生......
- 12.9万字10个月前
- 无限流BOSS是我的第二人格
- 【记忆是一个不可描述的东西,你真的没有失忆吗?】 很平常的一天,宋时堇的体内突然多了一个来自千年前的灵魂,那人自称是他前世的爱人,后来......
- 3.8万字8个月前
- 蛇莓穿越初中之穿越之旅
- 蛇莓穿越到了初三3班成为学生,从27章开始,蛇莓的名字改为了白珠樱,第29章开始模仿怪盗基德不更新了
- 115.9万字7个月前
- 逆天:谁家公爵搂着敌国公主睡啊
- 【脑洞西幻团宠权谋HE】【假花瓶真公主x腹黑绿茶公爵】年沂是维奥西皇室唯一的花瓶公主,从小受尽娇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大家都这样认为。直到......
- 1.3万字6个月前